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作者 / 里卡多·贝洛费奥雷(Bergamo大学教授),托马索·雷多尔菲·里瓦 翻译 / Revmira 排版 / 理查德克莱里恩 
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学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起的一项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项目,今天被我们称作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üre)。这个项目的主要发起者是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和海尔穆特·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其意图在于将马克思从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僵化图式中解放出来。我们将会在本文中尝试重构这一项目的开端,并将其根基追溯到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之中。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将会进而考察新马克思阅读对于马克思价值理论解读的原始进路。最后,我们将概述新马克思阅读存在的一些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展开批评与进一步的对话将会是卓有成效的。

新马克思阅读的诞生
按照许多种对于马克思的阐释,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劳动价值论,这种理论是对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修正。这些阐释往往倾向于关注《资本论》第一章的前两节,使得关于价值形式和商品的拜物教性质(fetish character)的章节仅仅扮演了补充性的角色。按照这种进路,马克思首先将商品视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然后他提出在交换价值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在被交换的商品之间共通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它们的可通约性的基础——也就是「价值」。最后,他将这个价值联系于劳动。这看起来可能是完整的;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里,我们就错失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全部要点。

大卫·李嘉图丨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在他之前和之后的那些经济理论在实际上区分开来的,正是价值形式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尝试对如下问题做出解答。为什么是价值?为什么价值仅仅是劳动的一种表达?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维度」,一个商品根据之而被交换的维度,什么是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之条件?此外,为什么价值的内容(即劳动)呈现出一种物的形式——也就是货币?[1]这些问题在《资本论》以及为《资本论》而作的预备性著作中(至少在《大纲》中)或多或少都能够找到踪迹,只有少数例外,但它们都未曾受到马克思的追随者与阐释者们的认真对待。
随着巴克豪斯、莱希尔特和施密特所做的贡献,这样的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变化。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战后新左翼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之时,他们从这一学派中脱颖而出,为联邦德国的马克思研究复兴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们提出的一般性问题包括马克思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其价值理论与政治经济学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其唯物主义的性质等等。但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对于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那种——之间的断裂的激进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断裂。一种新的、异端性的马克思解读诞生了。[2]
巴克豪斯可以被视为新马克思阅读的创始人。他在1965年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作为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大学开设的课程的一部分。在阿多诺的影响下,他阐述了一种新的马克思阐释的基本要素。四年后,他发表了他的论文中最为知名并且被翻译最多的一篇,那就是「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这篇论文是后来新马克思阅读研究计划的蓝图。巴克豪斯发现,在既往的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接受中,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倒退成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继而使得对于马克思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产生了误解。这些误解包括:将马克思的辩证的「呈示方法」(method of presentation)仅仅视为文字游戏或者历史性过程的逻辑映像;把他关于价值形式的论证当作对于货币的出现做的一个历史的、逻辑的概述,或者索性就完全把它忽略掉了。正如巴克豪斯所说:「『经济主义』的阐释势必会错失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意图:『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不过是与其他众多『经济学说』并列的一种而已。」[3]但巴克豪斯也明确表示,这种对于马克思的形式概念的误解并不是单纯地未能理解马克思所写下的内容,因为马克思本人也没有能够发展出对于价值形式的一种完整的解释。因此,理解价值形式辩证法的批判性意图的唯一方法就需要从马克思的一系列文本中的不完整表述出发,追踪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第二版中提出的不同版本的论证,对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加以重构。
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都将新马克思阅读的诞生日期定为1963年,那一年巴克豪斯在法兰克福的沃尔特·柯尔布学生宿舍(Walter-Kolb-Studentenheim)的图书馆中发现了《资本论》第一版的一份复制品:「经过初步观察,我们能够注意到在概念的建构上以及在价值理论问题的设定上存在着一种范畴上的差异,而这在第二版中仅仅被一掠而过了。」[4]巴克豪斯与莱希尔特、沃尔特·奥伊希纳(Walter Euchner)、G·迪尔、吉塞拉·克雷斯(Gisela Kress)、格特·舍费尔(Gert Schäfer)、迪特·森哈斯(Dieter Senghaas)组成了一个私人工作小组,并开始了文本上的考察。他们感到最有趣的东西就是在对于价值的「等价形式」的分析中存在的辩证矛盾,这种矛盾在《资本论》第二版中则更为难以察觉。黑格尔的「双重化」(Verdopplung)概念——卡尔·海因茨·哈格(霍克海默的一位助手)在那个年代分析了这个概念,马克思在第一版对于价值形式的呈示中使用了它——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逻辑意义。[5]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必须作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来处理,而不是作为某种模糊的、缺乏理论深意的哲学措辞。事实上,新马克思阅读的出发点就在于对马克思的呈示方法的批判性再发现。矛盾、双重化、假相(semblance)、现象显示(phenomenal manifestation)、实体等等,这些辩证概念都被正统的或「经济主义」的解读抹杀了。相反,对于新马克思阅读而言,这些概念成为了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 
阿多诺的遗产
莱希尔特认为,如果碰巧是某个没有听过阿多诺关于辩证社会理论的课程的人发现了第一版《资本论》,这一发现可能就不会有什么下文了。[6]这么说的理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性正在于阿多诺所说的「对起源的回忆」(the anamnesis of the genesis)。事实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代表的是一种作为主客观实在的社会之构造的理论。[7]正如巴克豪斯所解释的那样:社会是「客观的」,因为它是「涵纳并支配个别物的抽象普遍性」。[8]与此同时,社会又是主观的,「因为它仅仅凭借着人类才存在并再生产自身」。[9]
作为主客观实在的社会对于阿多诺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这是一种交换在其中实行着系统性支配的社会,它「以一种他律的方式是自然的延伸」。[10]在交换社会中,社会领域中的再生产类似于一种自然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特定的结构,个体的行动在其中建立了一个客观的领域,这一客观的领域支配了社会行动者自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摧毁了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对立。社会行动者所服从于的合法性是一种社会建构,但这种社会建构就如同一条自然法则那般作用于社会行动者之上:「历史生活的客观性就是自然历史的客观性」。[11]辩证社会理论必须表明这一点,那就是「社会——已经被独立出来的东西——反倒不再是可理解的;只有它变成独立之物的法则才是可理解的。」[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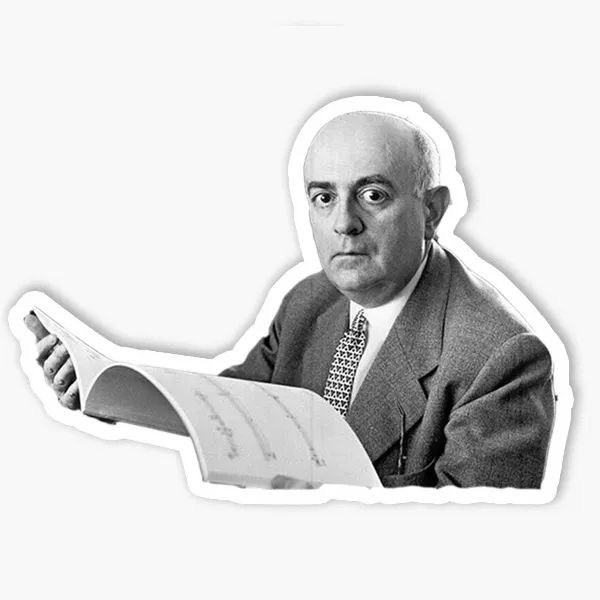
狄奥多·阿多诺丨Richardclam
按照阿多诺的看法,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整体,一个总体,一个普遍者:「没有任何社会事实在这种总体性中不具有一个位置。它对于一切个别的主体都是预先确立了的,因为他们服从了社会的『约束』(contrainte),甚至在自己中也是如此」。[13]而交换是内在地规定了每一个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的综合原则。[14]交换实现了「客观的」社会联系。[15]正是中介的原则通过一种抽象过程保证了社会的再生产,这种抽象「意味着将有待交换的产品还原为它们的等价物,还原为某种抽象的东西,但绝不是某种物质性的东西——就像传统的讨论所认为的那样」。[16]
阿多诺坚持认为,从对于交换的分析开始去理解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特征,即社会的自主化,这样做是可能的。每一次交换中进行的抽象都不是主观的,因为它「既独立于从属它的人的意识,又独立于科学家的意识」。[17]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着一种「还原为统一体」的原则,这种原则使得商品之间的交换成为可能。「使得商品能够被交换的是社会必要抽象劳动时间的统一体」。但这样一个统一体并不是通过一个由交换者执行的主观的抽象过程而得到规定的;相反,「抽象劳动时间摆脱了它的活生生的对立者(即交换者)」,这些交换者被内嵌在形成了自主性的社会关系之中。[18]货币「被朴素的意识当作自明的等价性形式,因而也被当作自明的交换中介而接受了下来,它解除了人们对于这样一种反思的需要」。[19]因此,在阿多诺看来,马克思关于价值、货币与资本的洞见,即将它们视为拜物教的特征,是理解社会自主化的钥匙:「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不过就是这个必然的抽象过程,它在经济学中将自身呈现为一个自然的过程,呈现为『一个物的自在存在』。」交换的辩证性就在于这一事实,那就是「一方面,商品拜物教是一个假相;另一方面,它又是终极的实在(äußerste Realität)。」[20]它是一种幻觉,因为那些被感知为自然物的东西是从社会关系中涌现出来的,在这些关系中,诸多社会行动者被整合起来;它是实在,因为向统一体的还原超越了行动者的意识,将一种「客观的」合法性强加于他们身上。
一种辩证的社会理论必须能够理解社会自主化的过程,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要能够解释「正在发生的对其社会起源的遗忘」。这一点在阿多诺与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的谈话中得到了精炼的表达:「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于起源的回忆。」[21]历史唯物主义揭露出社会成为独立之物的法则,以及对这一过程的理论性的遗忘。这就是阿多诺的批判社会理论的基础,也是新马克思阅读的出发点。
社会自主化和交换分析之间的关系是更值得我们回顾的,因为这一问题在阿多诺的著作中尚处于雏形。在1965年,阿多诺仍然表示有必要进行一种「对交换抽象的系统性的、百科全书式的分析」。[22]但他从未完成这一任务。莱希尔特令人信服地注意到,在阿多诺对于交换和真实抽象的反思中「已经总结了辩证理论的全部主题,但这一切主张还停留在断言的地步」;[23]「整个批判理论都取决于对这一『客观的抽象』做出澄清。如果使这个『客观概念』具体化是不可能的,批判理论中的其他一切概念…都将无法避免被指责为社会-理论性的思辨。」[24]由此可见,新马克思阅读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深化甚至奠基了阿多诺的批判社会理论的项目。

诠释学视角
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赋予了优先的地位,将它们当作理解他的晚期著作的一把钥匙,新马克思阅读则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作理解他的全部著作的钥匙。政治经济学批判被视为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在这一计划中,《资本论》以及预备性的手稿都仅仅是对于「资本的普遍概念」的分析。新马克思阅读又进一步主张,在对这一概念所做的呈示的形式中,资本的普遍概念还没有被马克思完全地发展开来,需要依靠马克思的其他著作来得到重构。为了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马克思的方法中的蕴意是必要的。我们不可能将呈示的形式同经济内容分离开来。我们必须遵循理论呈示的辩证形式,有时甚至有必要超出马克思的表述。这就是新马克思阅读与阿尔都塞创始的解读所共享的一个视角。正如施密特所说的那样:「尽管马克思对于自己的著作的理解可能的确很重要,但它通常远远不及马克思的材料分析在理论方面所给出的东西。」[25]
巴克豪斯早年的阐释立场认为对于马克思理论的误读是他的阐释者们的误解造成的。然而,在《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重构的材料》(Materiale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第三部分中,巴克豪斯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这些误解源于马克思本人。[26]深入分析马克思对于价值形式的不同呈示方式能够让读者同时从历史的和逻辑的两个方面来理解他的方法。遵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和《大纲》的部分章节中的分析,从基本的价值形式到货币的发展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逻辑的-共时性的发展。但如果读者遵照第一版附录或是《资本论》第二版,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按照巴克豪斯的观点,为了重构马克思的理论,我们必须采取一个不同的诠释学视角:我们不能仅仅参照马克思自己的文本;相反,我们必须理解马克思所尝试回答的问题,并进而选取能够最好地回答这些问题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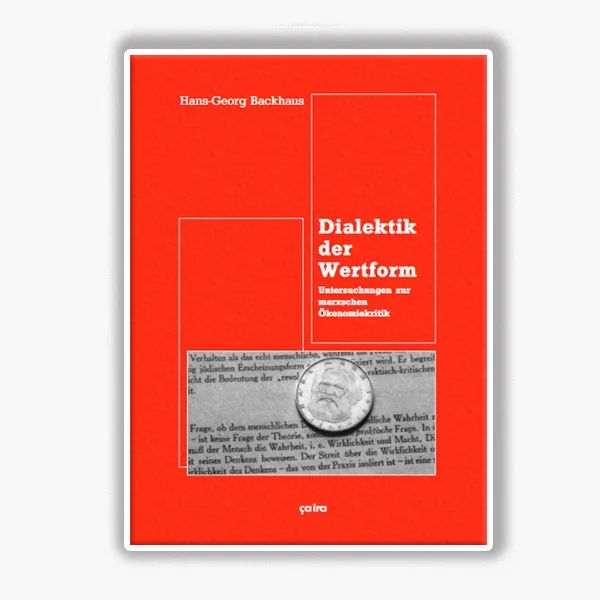
《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重构的材料》丨ca-ira
莱希尔特分享了巴克豪斯的进路,他表明在《资本论》中,关于「交换价值的日益自主化」的辩证呈示「只留下了最基本的梗概」。[27]对于莱希尔特来说,分析这一理论的不同阐述方式以及马克思的《大纲》中的基础概念的发展,也在重构一种严格的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计划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马克思阅读采取的另一个原创的阐释进路涉及的是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著作之间的关系。新马克思阅读的学者们反对阿尔都塞关于认识论断裂的诊断,并提出了对于马克思著作的一种一元的解读,他们使用了马克思本人的方法,从后继的社会形态所揭示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先前的社会形态——马克思阐述这一方法时著名地提出,人体解剖中蕴藏着猴体解剖的钥匙。新马克思阅读正是用这种方法通过晚期的文本来解读早期的文本,从而恢复了早期文本的意义,而不是像阿尔都塞提出的那样抛弃了它们,把它们当成是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28]正如施密特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长期以来都被认为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道主义内容,但它们只有通过对于《资本论》的历史-经济分析才可能得到充分的理解」。[29]
因此,举例来说,莱希尔特就坚持认为,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分析的市民社会和国家、资产阶级和公民、天国与尘世之间的颠倒这一过程必须根据对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来理解。这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批判需要理解为什么人类关系会以强制性的经济法则的形式呈现自身。与之相似的是,巴克豪斯表明,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通常被当作哲学残余而被丢弃的东西应该反过来被视为一种批判方法的首次尝试,这种方法辨识出了「存在-神学的、社会-形而上学的对象的同构结构,或政治和经济对象的同构结构」。[30]正如神学上的争论预设了尘世双重化为天国与尘世之间的对立一样,每一场政治经济学科上的争论都预设了交换的经济形式:价值、货币、价格,如此等等。「马克思的核心要求是,『那些』经济学家不应当预设『范畴』或『形式』,相反,他们应当『发生性地』(genetically)将它们发展出来」。[31]巴克豪斯发现,这种发生性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出现,在那本书中马克思触及了政治经济学的「未经反思的预设」:「马克思在这里谈论的是货币,按照『它』的功能,货币作为一个『非人的』(unmenschliches)主体而运作,也就是说,它使不平等的东西成为平等的,它『储存』了价值,并进行『转移』,等等。事物的、『外在于人的』事物的独立法则呈示了经济学的『客观的』…环节。」[32]

黑格尔与马克思
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他的逻辑学,被新马克思阅读视为理解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阐述的一个根本来源。施密特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批判」一词的含义开始的。他指出,对于马克思来说,没有任何社会事实本身可以通过传统的学科分界得到理解。真正的「知识的对象」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现象,因此就是作为总体的资本。但后者绝不能理解成把经验中被给予的生产条件当作知识的直接对象。相反,马克思是通过批评资产阶级的范畴与理论来推进的。[33]理论及其「客观的」内容是相关联的,但它们并不是同一个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研究的方法和呈示的方法在形式上是不同的。施密特解释道,探究的方法处理的是来自历史、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方面的材料,并通过知性的「分离」与「分析」来运作。相反,呈示方法则必须将这些孤立的数据结合在具体的统一中。同黑格尔一样,「展示」从直接的「存在」推进到中介性的「本质」,后者是存在的根据。本质性的实在必须在现象中显示自身,但这个具体的、对于本质的例示化和它的显示本身是有所区别的。即使是最为抽象的范畴也具有一个历史的、有规定的维度,但尽管如此,逻辑进程与历史进程仍然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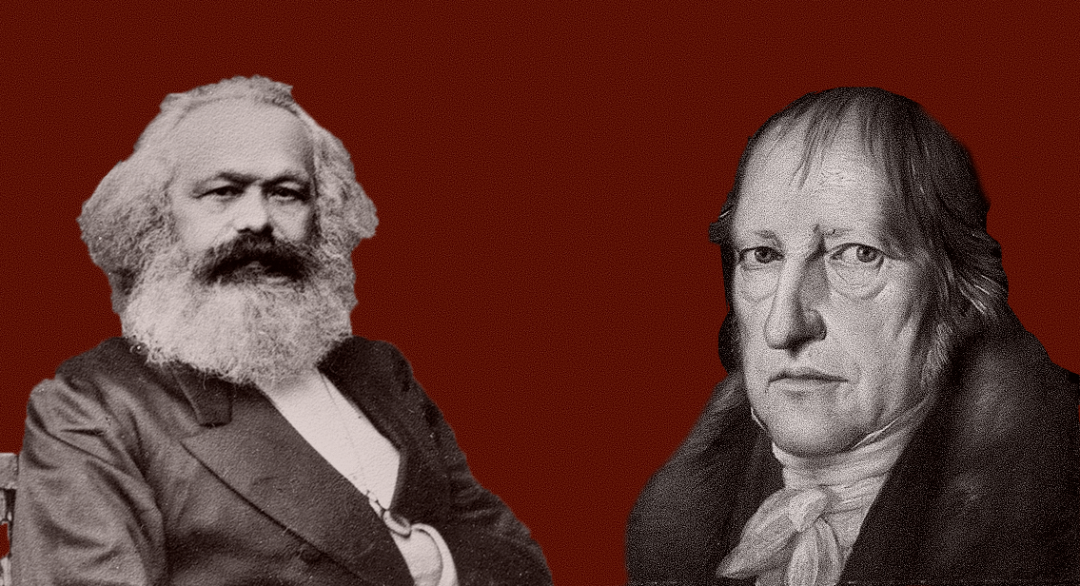
马克思与黑格尔丨无产者译丛
施密特在《历史与结构》中进一步处理了这些问题:
「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现实是一个过程:『否定的』总体性。在黑格尔主义中,这个过程显现为一个理性的体系。这是一种封闭的本体论,人类历史则从沉落到了其衍生物的层次,仅仅是其应用的一个实例。相反,马克思强调了历史发展的独立性与开放性,这种发展不能被还原为一种一切存在者都必须遵从的思辨逻辑。因此,『否定性』指的就是某种在时间上有限的东西,而『总体性』则意味着现代生产关系的整体。」[34]
逻辑环节相比于历史环节具有一种认知论上的第一性:如果没有提前对于资本具有理论性的理解,我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资本产生的历史性的前提。[35]但这并不会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使得范畴成为实在的存在根据。相反,范畴在知识中中介了实在。不过,对黑格尔的这一批判并没有取消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体系」观念所亏欠的东西。具体并不是立于人类理智面前的东西,而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它是这样一种知识,虽然在分析的方法中有其必然的基础,但却辩证地回避了事实与心理之间的二分。因此,马克思是以逻辑的方式,而不是以历史的方式推进的,因为他所分析的资本的形式设定了它自身存在的条件。

如果说施密特强调了黑格尔的方法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作用,莱希尔特则在本体论关系的方向上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论证。他声称马克思必须出于一个客观的约束而使用一种辩证结构性的论证,
「因为在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与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上的同一性。…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概念向绝对的扩展就是对于实在的恰切表达,这一事件在实在中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发生了。……对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言,是人类遵从着一个专制性的观念,因此这种唯心主义就比任何想要将普遍者当作某种主观的、概念性的东西接受下来的唯名论理论都更合乎这个颠倒的世界。它就是成为了本体论的资产阶级社会。」[36]
作为一种「陈述」或「展示」,呈示具有一种新的本体论意义。这种辩证方法的好坏与否取决于它对应于哪一种社会;只有在「普遍性以个体为代价自我申言」时,它才是有效的;事实上,它就是对于真实颠倒(real inversion)的哲学双重化。因此,唯物辩证法的标志性特征就是Methode auf Widerruf,即「回撤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当其存在的条件消失时,方法就必须将自身消解。[37]
莱希尔特同样突出强调了马克思在对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分析中所使用的统摄一切的主体(übergreifendes Subjekt)这一概念:
「价值时而采取时而抛弃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同时又在这种变换中一直保存自己和扩大自己;价值作为这一过程中统摄一切的主体,首先需要一个独立的形式,把它自身的同一性确定下来。它只有在货币上才具有这种形式。因此,货币是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38]
莱希尔特根据概念在黑格尔那里的绝对性来理解资本的扩张着的、支配性的力量,概念「在哲学的基地上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秘密:将一个衍生的实在颠倒为一个第一性的实在。因此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概念向绝对的扩展就是对于实在的恰切表达,这一事件在实在中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发生了。」[39]
在巴克豪斯那里也可以发现相似的论点。黑格尔是马克思对于商品、货币与资本理论的「革命化」的开端,这正是因为他以一种辩证的结构揭示了理论本身。然而,黑格尔只不过是第一步,因为他未能分析商品的二重性。(然而,巴克豪斯同样指出,黑格尔的确在一些尚未发表的、因而也不为马克思所知的著作中很好地看到了这种两面性。)对于巴克豪斯来说,黑格尔重复了李嘉图和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缺陷:对起源的遗忘,尽管他的范畴装置给了他完成这一任务的潜在的理论手段。[40] 
马克思的方法与对前货币价值理论的批判
新马克思阅读重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在于对将马克思的方法理解为一种逻辑-历史方法的阐释提出的质疑,这种阐释从恩格斯对于「简单商品生产」的讨论那里就开始了,并被马克思主义传播开来。按照巴克豪斯的看法,恩格斯1859年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论以及他1895年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增补」导致了对于马克思的陈述方法的历史化。在他的书评中,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呈示的逻辑方法说成是「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41]在「增补」中他又将这同一种历史的方法应用于解决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矛盾,使价值在简单商品生产这一历史阶段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交换比率系统。[4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丨人民出版社
对巴克豪斯而言,简单商品生产的概念是对于马克思产生了两种不同阐释的根源所在,这两种阐释分别是:逻辑-历史阐释与假想阐释。按照前者的观点,价值理论是对于简单商品生产之法则的逻辑理解;货币在社会中历史性地产生,而价值形式就是这一产生在逻辑中的映像。在后者看来,价值理论首先并不是历史性的,而是资本主义中的价格的假想性近似值。价值是一般交换社会中交换比率的规律。这一步骤必须由以下第二步作为补充,那就是增设第二个近似值,即生产价格,它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比率的规律。论述价值形式的段落又一次被解读为从交易到货币交换的过程的一个历史性的补论。[43]
尽管这些阐释有所不同,但它们共有着一种观念,那就是认为存在着一个没有货币的一般交换(generalized exchange)的初始阶段,并且都对价值形式做出了历史化的解读。巴克豪斯给这两类观点贴上了「前货币价值理论」(pre-monetary theories of value)的标签,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必须被理解为对这些前价值的或非价值的进路的批评:「马克思试图表明,无矛盾地建构一种在分工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前货币市场经济的概念是不可能的。……前货币商品的概念是无法设想的。」[44]从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到一般价值形式的过程表明,一种无需货币的普遍交换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在导向价值形式的辩证展示中,马克思的交换过程必须被理解为「流通」(Zirkulation),它是交换的形式规定性,在其中(不是产品而是)商品假定了货币形式——也就是价格形式。「流通」在这里必须同「交换」(Austausch)本身区分开来,后者是一种超历史的概念,一种除去了任何实效化实存(例如「劳动」或「产品」)的抽象。接下来我们就得到了商品交换(它在本质上就是货币的)和产品交换(它则不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理论中的批判性内容可以与客观(古典或马克思主义)和主观的价值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两条进路都共享了同一种观念,那就是为了理解交换并建构一种价值理论,从货币中进行抽象是必要的,货币就这样被还原为了一层面纱。其结果是一个双重的失败:它们将资本主义自然化,同时又混淆了货币在社会中的作用。在这个社会中,通过用货币这一普遍等价物来交换商品,私人的、自主而独立的公司最终不得不确认从普遍流通中产生出来的价值。前货币价值理论创造了一个双重的价值量度体系:首先是依据商品之可通约的维度(劳动或效用);其次是依据货币。这些量度的维度是没有中介的。外在的、「客观的」货币交换现象与价值的维度是脱节的,价值在理论上被预设为是独立于货币的。正如巴克豪斯所说,「在主观价值与客观的交换价值之间、在被主观地阐释的价值『实体』与被客观地预期的价值『形式』存在着一条裂缝」。[45]
此外,对于巴克豪斯来说,马克思的批评还可以用来针对大部分价格理论,还有那些去除了价值维度的学者,譬如斯拉法的许多追随者。他们认为由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的异质物体间如何通约的问题是无意义的。但在巴克豪斯看来,疑难并没有通过唯名论的货币理论得到解决。只有在对货币所量度的维度加以规定之后,货币才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抽象的记账单位。在巴克豪斯之后,我们必须承认,价值维度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维度,事物在其中会呈现出「社会-自然的性质」。
巴克豪斯所呈示的马克思发展了一种强有力批评,它驳斥了一切将资本流通回溯到一个抽象的前历史或超历史交换的价值理论,同时,他也提出了一种超越一切形式的唯名论的货币理论。货币被巴克豪斯看成是商品流通中不可或缺的,它自主地(在行动者的意识之外)建构了对于私人劳动的社会协调。被理解为一种用于简化交换行为的约定成俗手段的货币概念在他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商品的双重化
价值与货币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商品的理念与实在的双重化」,这是莱希尔特提出的一个主要论题。在巴克豪斯的第一篇论文基础上,莱希尔特表明,马克思的呈示的新颖性在于将商品展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直接统一。只有当商品的两个方面在交换过程中按照它们之间现实的关联而被纳入考虑时,这一内在的矛盾才会在外表上被表现出来。政治经济学要么在其具体性的方面、将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来考察商品,要么凭借一种主观的、纯粹心理性的抽象行为、将商品作为价值来考察商品。马克思对于价值形式的研究则表明,主观的还原实际上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只有通过深入地研究价值如何在交换价值中以现象的形式显示自身,这种抽象才能得到理解。
莱希尔特强调交换总是在两个不同的具体事物、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发生,这是他的论证的开始。商品从不会直接地将自身展示为人类劳动的表现,尽管每一个商品都具有价格,并且作为价格,商品是可以比较的:「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因为它不是将货币形式从私人劳动的结构中演绎出来;马克思试图表明的是,政治经济学在价格形式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对于价格形式它不得不外在地来理解。」[46]在商品交换的每一次均等化中,等式左侧的商品在等式右侧的商品的形体具体性中展示出了自己的凝结化的价值。价值的两个维度是被同时纳入考虑的:「这一商品获得了一种不同于其自然外形的价值形式,而另一个不同的商品则在其直接的自然外形中被视为『凝结的同质人类劳动』的现象化形式」。[47]商品之中的内在对立通过商品在交换价值中的双重化找到了它的现象显示的形式:等式的一侧成为了(以相对的形式出现的)使用价值,它在另一个商品的形体中(以等价的形式)展示自身的价值,而这另一个商品则只能被算作价值的客观化了。抽象人类劳动在一个形体中获得了一个可见的化身,它可以在这个形体中将自身表现出来。它的价值也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思的实事」(,而且还取得了一种似物的实存。价值的抽象在一个自主的对象在中成为了具体,这个自主的对象作为商品和其他一切的使用价值对峙起来。「商品是物(Sache)。它们必须以物的(sachlich)方式或必须在它们的似物的(sachliche)关系上表示自己是什么。」[48]价值展现为货币与价格,抽象劳动在普遍等价物中获得一种似物的形式,这是马克思对于价值形式的阐述的理论结果。
莱希尔特紧跟马克思的辩证演绎,从简单价值形式中推导出普遍等价形式(并进一步推导出货币形式),从而表明了在交换过程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是如何被扬弃的。一方面,商品生产中花费的私人劳动必须被展现为社会劳动。另一方面,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劳动是同一个主体的不同形式的活动。在普遍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必须达到一个近似的结果,这一结果需要一个古怪的情况来实现:劳动获得了抽象人类劳动这一超感性的属性,而这个劳动也正是价值实体。
抽象劳动——也就是处在成为社会劳动过程之中的私人劳动——的存在需要商品作为使用价值而生效;也就是说,需要具体劳动被确认为社会分工的一部分。这个矛盾就是一个社会的种差,在社会中,劳动不是在生产本身中直接地就是社会性的。在众多独立生产者之间的私人交换体系中,社会劳动的发生仅仅归功于对于商品市场的(货币性的)最终确认:「普遍等价形式的存在是这样一种形式,这个矛盾在这一形式中被分解,从而也被扬弃到这个形式之中。」[49]
只有一种商品发生了变形,使得在这种商品中生产所耗费的劳动直接地就被计为社会性的,才会产生对于私人劳动的社会确认。这个商品就是普遍等价物:货币。只有货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才能确立生产一个个别商品所耗费的劳动的社会必要性。商品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不得不以货币的形式表现自身的原因就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具有的两种性质之间的矛盾。正如莱希尔特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基础是将货币从交换过程的结构中演绎出来,同时也是将普遍等价形式演绎出来,这种普遍等价形式被理解为作为形式的价值、作为实体的价值,以及作为量的价值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
在呈示了商品在简单流通中的双重化后,莱希尔特发展了巴克豪斯对于简单商品生产概念的批判中的「积极方面」。莱希尔特提出了一种对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理解,即「以最为抽象的形式实现了的货币演绎的进一步具体化」,[50]它考察了「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之间的逻辑关系。在简单流通中,社会成员仅仅将他们自己表现为交换者。然而,流通不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自主的过程。商品在流通中被交换,但它们的生产是被预设下来的。一旦商品被售出,它们就离开了流通领域,并进入了消费领域。[51]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节中发展的对于货币不同功能的呈示被莱希尔特理解为货币作为抽象财富的似物存在逐步取得独立的过程。《大纲》中马克思对于贮存的分析成为了一个关键。为了作为价值而获得独立性,货币需要退出流通,但在流通之外,货币仅仅是潜在的(抽象的)财富:「作为一个物(即货币)而存在的普遍财富的实在存在于它自身之外,存在于构成了它的实体的诸个别物所组成的总体之中。」[52]货币一经采取了资本——获得了M–C–M'这一运动形式的、自我增殖的价值——的形式,矛盾就被扬弃了:「在这些形式里面的每一种之中,它(作为资本的货币)都自在地保存了交换价值。因此,它不仅在获得了货币的形式时是货币,在它具有商品的形式时也是货币。…在这些形式里面的每一种之中,它都是自为的。」[53]
莱希尔特遵循了马克思的论点,他表明简单流通是一个寓居于自身之外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外显,而人的天赋权利的伊甸园是一个假相,它掩盖了对于商品生产中耗费的无偿劳动的占有。流通不具有自主的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头三节呈示的价值理论并不是对于商品生产体系的描绘,在这一体系中生产的主客观条件仍然是未分离的。这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表面:被马克思作为前提而开启了呈示的商品随后被设定为了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当然,这正是马克思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开篇所提出的东西,这篇手稿是马克思运用「设置预设」(positing the presupposition)方法最清晰的范例之一。此外,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所进行的「劳动」是雇佣劳动者的活劳动。在《大纲》的一个著名段落中,马克思称之为运动着的抽象劳动(abstract labour in mo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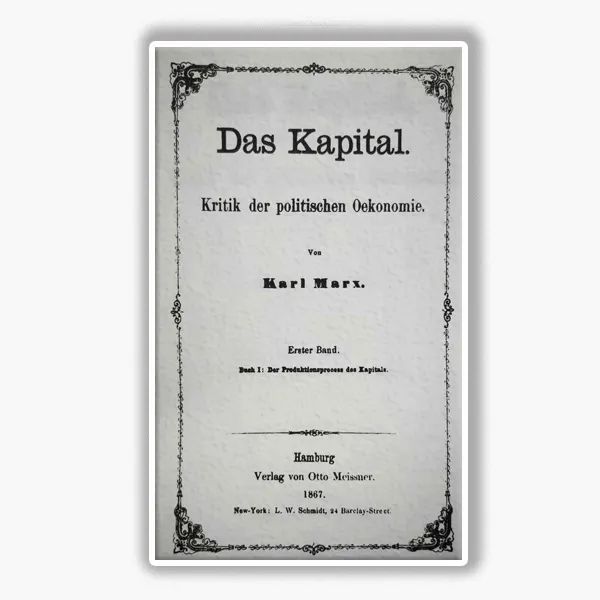
马克思《资本论》丨Wikipedia 
社会的「客观」构造
仔细阅读莱希尔特和巴克豪斯会发现,根据劳动耗费的规定性的形式,不可能先于现实交换去规定在生产中耗费的、将会取得货币形式的直接私人劳动的量;也就是说,通过由被认定为直接社会性的(immediately social)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直接私人的(immediately private)劳动将会被确认为间接的社会性的(mediately social)。马克思在《大纲》货币章中对蒲鲁东的批判被视为对于理解劳动的二重性质具有基本意义。如同巴克豪斯所表明的那样,
「马克思演绎出了『社会劳动』的概念,并发现了这种劳动的形式与『现实』的、具有私人属性的劳动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这一矛盾是『劳动将自身展现为价值』的理由,或者换句话说,是货币之存在的理由。」[54]
对蒲鲁东式社会主义的批判,按照同样的道理同时也是对于价值形式理论的展示,是将货币形式从由私人、自主的生产者组成的社会所具现的社会构造中推导出来的概念性演绎。没有对于货币和劳动耗费的形式之间联系的理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失去了自身的特殊性,从而倒退回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按照后者的看法,被生产出来的价值的量能够通过生产中的一个主观的量度行为得到规定。某种劳动价值论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表明的那样,在资本主义中,「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而劳动的社会性「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55]对于马克思而言,价值理论是一个超个体的维度,它独立于生产中的行动者的意识而发生。劳动的抽象化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不能被还原为一种心理性的一般化。抽象劳动不能同作为超历史的目标导向活动的劳动混淆起来。这样的劳动是一个心理性的抽象,如果没有取得一种有规定的社会形式就不会存在,而抽象劳动却是劳动在社会中获得的特定形式,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通过一个在私人生产者之间进行的货币交换的体系而开展的。正如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经常重复的那样,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在于理解「价值法则是如何自我申言的」,因而也就是在于认识到经济行动者背后所发生的「客观」过程。
生产的个体维度与交换中发生的社会确认(social validation)的超个体维度之间的裂缝对于理解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却将拜物教简化为有关价值历史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陈词滥调。[56]我们之所以可以谈论拜物教性质,是因为除了通过商品和货币之间的交换来进行协调以外,对于私人生产过程不存在任何预先的协调。货币是确立私人生产过程间的社会联系的媒介,因而也在个体行动者的「背后」和「意识之外」创造了社会。社会联系是被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也就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体系所决定的。
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假定普遍的商品交换和价值形式是不成问题的。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它无法理解物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的「颠倒」和「错位」。巴克豪斯说道,「学院经济学被迫把价值或者价值形式处理成『人以外的物』(Sache außer dem Menschen):他们把货币和数学形式作比(比如线或数字),这些形式是否能够被人类推导出来是很成疑问的。」[57]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巴克豪斯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描述为「错乱的形式」(Verrückte Formen)。经济范畴是疯狂的、错乱的、错位的形式。它们是可感物在超感性物中的变换(transposition)与投射。经济学理论仅仅知道这一疯狂和错位的结果。经济学理论的批判有任务展示这些错乱的形式的起源,它们在人中的起源。
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重构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他们理解了阿多诺所形容的自主化过程的含义。自主化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这一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由于这一矛盾,劳动的社会化就是独立于劳动耗费而发生的,这一过程通过私人生产者之间的货币交换的体系而进行,这也就创造了社会运动的自主形式:拜物教性质。凭借着对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的这种解读,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就可以将阿多诺的设想中批判社会理论的关键部分付诸实现:不仅要破译社会自主化的「社会起源」,而且要理解对起源的「遗忘」是如何发生的,正是这种遗忘导致了拜物教。对于市场上的「物」的普遍货币性的商品交换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所具有的历史上特定的社会特征表面上看起来变成了这些「物」的「自然」属性。对于社会自主化之起源的遗忘发源于这个幻象,这个「虚假的显象」,一个假相。这样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化来自于这个「客观」现实本身,来自于现实本身的拜物教性质。对于起源的遗忘就这样完成了。

批判与对话
我们认为,对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问题、对于价值形式的强调,以及在更为一般的层面上,新马克思阅读所提出的概念视域,对于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们认为仍然有和新马克思阅读对话的空间,或许还可以对它提出一种批判。[58]目前为止本文大部分篇幅都是在进行解释性的工作,但我们认为考虑一些疑问是十分重要的。一些疑问与马克思本人的推论中存在的困难有关。另一些则涉及到新马克思阅读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坚持,似乎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像他所打算的那样,同时也是一种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59]这样做的风险在于找回了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但又将他和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这是一种学院式的划分,但对于马克思本人却是完全外在的。
我们认为,新马克思阅读对于马克思在抽象劳动、价值和货币上的理解(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到三章)的复杂性缺少关注,在马克思如何将资本奠基为一种社会关系(第四到七章)这一问题上也不够重视。如果我们重构马克思关于价值、货币与资本的辩证法,我们就会看到商品中的二重性,即价值与使用价值。与生产它的劳动的二重性相对应。就劳动生产了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而言,劳动(作为活动)是「具体」的。困难在于,使用价值与具体劳动并不是同质的,因此它们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相反,价值对于马克思来说却是「单纯的」被凝结的劳动:一个同质的量,其本身就是可通约的,至少在我们看向整个商品世界而不是某个单一的商品时的确是这样。新马克思阅读在坚持可通约性仅仅是从交换中产生的时候便远离了马克思。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一下这个问题。在第一章的第一和第二段中,「价值」被掩盖在商品中,不过是一个「幽灵」。这个「纯粹社会的」存在物是如何获得物质性的存在的,这一点还没有被表明。在发生交换之前,看起来在我们面前的东西不过是具体劳动,这些劳动在一定的不可通约的使用价值中被「体现」出来。在第三章中,马克思继续证明存在商品和货币的「双重化」,这一「双重化」与商品中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对应的。一旦一个特定的商品——比如金子——发挥了普遍等价物的作用,价值的「幽灵」就「占据」了一个「身体」。货币现在成为了价值,被体现在黄金的使用价值之中。商品中包含的抽象劳动被展现为成为了货币的黄金中所体现的具体劳动,私人的劳动成为了社会性的。货币是普遍等价物,它在事后确认了「直接的私人的」(而仅仅是「间接的社会性的」)抽象劳动。但它同时也是价值的「个别的化身」(Inkarnation),是唯一一种能够被算作直接的社会性的劳动,也就是生产(作为货币的)黄金的劳动的产物。在这里,「作为商品的货币」是将价值反过来联系到劳动之上的本质性纽带。这个要点并没有得到新马克思阅读的注意。
由于初步地生产出商品的(抽象)劳动与生产出作为商品的货币的(具体)劳动的这一连接或等价性,马克思就为将货币量转译为劳动量的可能性做出了奠基,为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这一概念创造了条件。这种等价性是通过商品市场上的交换,而不是单纯在生产中得到确立的,在坚持这一点上,新马克思阅读是正确的。然而,马克思始终坚持认为,可通约性并不是从货币传导到商品上的,而是沿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商品的价值在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展现」出来,这是一个由内到外的运动:它是将内容「表现」到形式之中。生产和流通之间的统一是在市场上得到确立的,但这一统一现实化了一个由内(生产)到外(流通)的运动。这种张力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呢?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观点是,作为人类的活劳动凝结而成的抽象物,价值——在生产之后,在现实交换之前——被计为由行动者所预期的「观念上的」货币量。(它是一个表象[Vorstellung]。)商品带着价格标签进入市场。一方面,商品和货币之间的等价性是一种实质上的均等。另一方面,「观念上的」货币量是对于作为「实在」货币的黄金的一种「心理表象」。货币是价值量的「外在」标尺;「内在的」尺度则是在生产中花费的劳动时间(的社会必要量)。然而,后一个维度必须在流通中以货币的形式才能得到确认。商品交换是价值量度行为真正发生的场所。[60]
巴克豪斯在提出普遍的「商品流通」必须被设想为内在地就是货币性的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交换(Warenaustausch)和流通本质上就是货币性的。「交换」并不能被理解为以物易物式的「产品交换」(也就是被理解为直接的产品交换[unmittelbare Produktenaustausch]),正是以物易物中固有的难题产生了货币,作为对于这些难题的解决。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提出的「货币价值」的量的规定性被证明是决定性的。货币的价值是对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货币性表现」的颠倒:在一个单位的货币中展现了多少劳动时间。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节中,货币的价值被固定在生产黄金这一时间点上——也就是说,被固定在作为货币的黄金进入流通中的这个点上。黄金最初只是作为单纯的商品,和所有其他商品进行交换的。这种交换并不是货币性的;它是直接的以物易物。(德语在这里是相当明确的:直接的物物交换[unmittelbarem Tauschhandel]。)一旦黄金以这种方式作为「劳动的直接产品」进入市场,在对于它的生产这一根源中,它就作为货币而运作了。从这时起,货币的价值就可以被视为在最终交换发生前就被给定了。交换的完成在生产过程中、在交换之前就已经对生产者施加了价值的约束,这样一来,活劳动就必然已经被视作抽象劳动了。
在《资本论》最初三章的推论中,货币是一种商品这一事实并不是很成问题的。在这里我们处于这样一个层级,在这个层级上,明确的认识对象是作为商品而被生产出来的,而货币是作为普遍等价物而被生产出来的。换句话说,生产是被预设下来的。当我们移动到另一个层级,认识对象成为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样一个一个时间性过程,它从劳动力的买卖开始,并推进到生产的隐秘之处,到了这时,这个论证就变得不再牢靠了。我们的观点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开始处于一个不再能够假定货币是一种商品的世界。理论上的挑战正在于如何将货币性的(劳动)价值论延伸到一种货币性的(资本主义)生产理论。按照这样的思路,有可能提出一种论证,以表明生产需要由一种非商品的(银行的)劳动力买卖金融来预先确认(ante-validated)。在这种情况下,活劳动作为抽象物将会在最终交换发生之前就被一种货币性的过程造就为同质的。这样一来马克思关于从生产到交换的运动的论证就会完全被抢救过来。早期的新马克思阅读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一领域,使得马克思的商品和货币理论发生了中断。
另一个新马克思阅读在马克思的论证阶段过快地中断了的论点关系到资本主义总体性的构成(Konstitution)。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界定了商品和货币的世界的那种颠倒得到了证实和深化。在劳动力市场上,人类成为了他们售卖的商品的「人格化」,成为了劳动力或「潜在的」劳动,工人则完全成为了这种商品的附属物。在生产中,活劳动本身被化身为「过程中的价值」的资本所组织与形塑。所以,作为雇佣工人生产出抽象的资本主义财富的抽象活动,活劳动才是真正的主体,而执行它的具体的人类则只是它的谓词。
为了真正地自我奠基,价值必须由价值产生出来,赚取剩余价值。但死劳动并不能产生更多死劳动。资本必须将这样一种活动「内化」到生产之中,这种活动能够将少量的死劳动转变为更多的死劳动:也就是将仅有的「他者」转变为死劳动,那就是人类的活劳动。作为一个幽灵,价值必然会转变为资本,一个吸血鬼。借用克里斯·阿瑟的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表述来说,工人被当作一个内在的他者(活劳动)含括在资本(死劳动)之中。
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自我增殖的价值」——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似乎越发一致了,它们都试图现实化自身,同时再生产它们整个的存在条件。正如阿多诺说过的那样:全体即虚假(Das Ganze ist das Unwahre)。某种意义上说,新马克思阅读是对于这句话的一个漫长的注解,也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确立最终基础的尝试。然而,资本那僵尸般的生命取决于一个社会条件:资本必须在阶级斗争中胜过生产。它必须从工人那里吸食生命,这样它才能如同「不死者」一般死而复生。工人能够抗拒自己被整合为资本的一个内在环节,如果冲突转化为对抗,这个可以逾越的「壁垒」或「限制」(Schranke)就会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Grenze)。关键在于,如果不去压榨劳动力,就不可能有劳动。不去「消费」工人自己的身体这个劳动力的活的载体,使用劳动力就是不可能的。资本的生产只能归功于这个特定的「消费」,这个特定的「消费」又创造了一种特定的「矛盾」。[61]而这才是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的独特理论的真正基石,它将生产中新增的价值回溯到工人消耗的活劳动之中。(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论证并不需要货币成为一种商品。)
对起源的遗忘——阿多诺留给新马克思阅读的遗产——在这里发展成了一种从资本的根源这一视角观察它的悖论性现实的方式,而它的根源就是活劳动,这种劳动是从劳动力的活的载体即雇佣工人那里剥削得来的。这就是关于资本构成的批判性的、革命性的话语。/
注释与参考文献:(滑动查看更多)
[ 1 ] 困扰着非德语马克思研究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于,很少有译本在处理所有关键范畴时都能保持严格——这些范畴大部分都来自黑格尔,尽管不是全部。(一个例外是最近出版的罗伯托·菲内斯基的意大利语译本。)在本文中我们采用了里卡多·贝洛费奥雷在'Lost in Translation: Once Again on the Marx–Hegel Connection', in Fred Moseley and Toni Smith eds, Marx's Capitals and Hegel's Logic, Brill, Leiden and Boston MA, 2014中的约定,但略有改动。例如假相(Schein)一词和黑格尔那里一样与被看成本质的表面现象有关。这样来描述资本主义的现实就意味着它不过是幻觉,一个单纯的假相。动词scheinen(映现)在这里会被翻译为「to seem」。现象(Erscheinung)、「显象」或「(现象)表现」则与那些现象如何显现或显示自身(erscheinen)有关。它是本质的必然表现;是后者不得不在现象层级上显现或显示自身的方式。当我们使用「显现」或「显象」这样的术语时,读者应当注意我们指的是erscheinen和Erscheinung。Darstellung会翻译为「阐述」(exposition)、「展示」(exhibition)或「呈示」(presentation)(同时用相关的动词来翻译darstellen)。它关系到的是体系的过程性展开,这从对整体进行逻辑重构的角度看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被展示出来的东西被辨认为如此这般的,辨认为一个复杂的中介过程的结果,那么它就是一个「显象」或「表现」。如果不是这样,它就是一个「幻相」或者「假相」。不幸的是,在许多翻译中Darstellung都被翻译为「表象」(representation),而darstellen被翻译为「表征」(to represent),这是错误的,因为「表征」和「表象」对应的是vorstellen和Vorstellung。表象是心理的或概念性的表象:一个观念上的预期,或者行动者把握资本主义形式的方式。有关翻译的更多约定会在下面进行阐明。
[ 2 ] 新马克思阅读一词是巴克豪斯在《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重构的材料》第三部分中使用的,收于Hans-Georg Backhaus, ed.,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11,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1978。后来的经典著作还有:莱希尔特的Neue Marx-Lektüre. Zur Kritik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Logik, VSA Verlag, Hamburg, 2008;Ingo Elbe, Marx im Westen. Die Neue Marx-Lektüre in der Bundesrepublik seit 1965, Akademie Verlag, Hamburg, 2008;Michael Heinric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ree Volumes of Karl Marx's Capital,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12;以及'Between Marx, Marxism, and Marxisms – Ways of Reading Marx's Theory', http://viewpointmag.com/2013/10/21/between-marx-marxism-and-marxismsways-of-reading-marxs-theory。对1970年代德国关于马克思的辩论的进一步深入分析,参见Roberto Fineschi, 'Dialectic of the Commodity and Its Exposition: The German Debate in the 1970s – A Personal Survey', in Riccardo Bellofiore and Roberto Fineschi, eds, Re-reading Marx: New Perspectives after the Critical Edition, Palgrave, New York, 2009。
[ 3 ] Hans-Georg Backhaus, 'On the Dialectics of the Value-Form', Thesis Eleven 1, 1980, p. 99.(中译文参见《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1辑第68页——译注)
[ 4 ] Hans-Georg Backhaus, Dialektik der Wertform. Untersuchungen zur Marxschen Okonomiekritik, ça ira Verlag, Freiburg, 1997, p. 29. 也参见Reichelt, Neue Marx-Lekture, p. 11。
[ 5 ] Backhaus, Dialektik der Wertform, p. 30.「双重化」的范畴也可以在1872年的版本中找到:不是在第一章关于价值形式的阐述中,而是在第二和第三章。
[ 6 ] Reichelt, Neue Marx-Lekture, p. 11.
[ 7 ] 关于新马克思阅读和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参见Werner Bonefeld,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On Subversion and Negative Reason, Bloomsbury, London New York, 2014。
[ 8 ] 当马克思使用形容词gegenständlich时,他的意思经常是「变成对象性的」(becoming objective),例如在人类面前的对象性(这种东西在作为活动的劳动这一过程性环节中有其起源)。这一术语难以翻译为英语。在这里和下文中我们会将它翻译为加引号的「objective」。
[ 9 ] Hans-Georg Backhaus,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Marxian Social Economy as Critical Theory', in Werner Bonefeld, Richard Gunn and Kosmas Psychopedis, eds, Open Marxism, vol. 1, Pluto Press, London, 1992, p. 57.
[ 10 ] Theodor W. Adorno, 'Introduction', in VV.AA.,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Heinemann, London, 1976, p. 12.
[ 11 ]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p. 354.
[ 12 ] Adorno, 'Introductio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p. 15.
[ 13 ] Ibid., p. 12.
[ 14 ] 对于阿多诺来说,总体性是一个客观角度的(a parte obiecti)范畴,它预先决定了客体本身。因此,融贯而无矛盾地描述社会对于事物自身来说是不充分的。这就是为什么阿多诺的总体社会概念不能等同于汉斯·阿尔伯特的庸俗观念「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参见The Positivist Dispute, p. 175 n26。
[ 15 ] Theodor W. Adorno,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Polity Press, cambridge, 2000, p. 31.
[ 16 ] Theodor W. Adorno, 'Sociolog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p. 80.
[ 17 ] Ibid.
[ 18 ] Theodor W. Adorno, 'über Marx und die Grundbegriffe der soziologischen Theorie. Aus einer Seminarschrift im Sommersemester 1962', in Backhaus, Dialektik der Wertform, p. 507. V. Erlenbusch 和C. O'Kane的英文翻译将在期刊《历史唯物主义》上发表。
[ 19] Adorno,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p. 32.
[ 20 ] Adorno, 'über Marx und die Grundbegriffe der soziologischen Theorie', pp. 507–8.
[ 21 ] Alfred 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orperliche Arbeit. Zur Epistemologie der abendlandischen Geschichte, VCH Verlagsgesellschaft, Weinheim, 1989, p. 223.
[ 22 ] Ibid., p. 226.
[ 23 ] Reichelt, Neue Marx-Lekture, p. 30.
[ 24 ] Helmut Reichelt, 'Marx's Critique of Economic Categories: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 of Validity in the Dialectical Method of Presentation in Capit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4, 2007, pp. 6–7.
[ 25 ] Alfred Schmidt, 'On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in the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VV.AA., Karl Marx 1818–1968, Inter Nationes, Bad Godesberg, 1968, p. 94.
[ 26 ] Backhaus, Dialektik der Wertform, pp. 129–212.
[ 27 ] Method?', in Werner Bonefeld, Richard Gunn and Kosmas Psychopedis, eds, Open Marxism, vol. 3, Pluto Press, London, 1995, p. 58.
[ 28 ] Helmut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sbegriffs bei Marx, Europäische Verlangsanstalt, Frankfurt am Main, 1970, p. 24.
[ 29 ] Schmidt, 'On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p. 94.
[ 30 ] Hans-Georg Backhaus, 'Some Aspects of Marx's Concept of Critique in the Context of his Economic-Philosophical Theory', in Werner Bonefeld and Kosmas Psychopedis eds., Human Dignity: Social Autonomy and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shgate, Aldershot, 2005, p. 18.
[ 31 ] Ibid., p. 22.
[ 32 ] Ibid., p. 24.
[ 33 ] Schmidt, 'On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pp. 95–6.
[ 34 ] Alfred Schmidt, History and Structure: An Essay on Hegelian- Marxist and Structuralist Theories of History, MIT Press, Cambridge MA, 1981, p. 31; 翻译有改动。
[ 35 ] 对于施密特来说,这就是为什么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的章节唯独包含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末尾中:「如果马克思不首先从理论上把握资本的本质,他就无法成功地对资本的产生所包含的历史预设的内容加以展开。他甚至没法知道这些内容要到哪里寻找和怎么寻找。」 Schmidt, History and Structure, p. 33.
[ 36 ]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sbegriffs bei Marx, pp. 76–7, 80.
[ 37 ] Ibid., pp. 81–2.
[ 38 ]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One, Penguin, Harmondsworth, 1976, trans. Ben Fowkes, p. 255; 翻译有改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180页,有改动,原文中将übergreifendes Subjekt翻译为「扩张着的主体」——译注)。马克思使用übergreifen一词有双重含义。按照黑格尔《全书逻辑学》的译者的说法,第一个含义可以被理解为「to overgrasp」(统摄):它指的是扬弃,思辨的把握,它「返回自身并在自身中包含」它的辩证阶段诸环节中的对立面。普遍性「统摄」了个别者和单一者,思想也以同样的方式「统摄」了有别于思想的东西。因此,发展为精神的主体在它的把握(grasp)中包含了对象性和主体性。第二个含义是「扩张着的」和「凌驾一切的」,近似于「支配性的」(dominant)——福克斯(Fowkes)使用的一个术语。
[ 39 ]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sbegriffs bei Marx, p. 77.
[ 40 ] 参见Backhaus, Dialektik der Wertform, pp. 302–3。
[ 41 ] Frederick Engels, 'Review of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16, Lawrence & Wishart eBook, 2010, p. 475(中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第603页——译注)。
[ 42 ] Frederick Engels, 'Supplement to Capital, Volume Three',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7, Lawrence & Wishart eBook, 2010, p. 887
[ 43 ] Backhaus, Dialektik der Wertform, p. 277ff.
[ 44 ] Backhaus, 'Materialie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 3', p. 150.
[ 45 ] Hans-Georg Backhaus, 'Sulla problematica del rapport tra 「logico」 e 「storico」 nella critica marxiana dell economia politica', in his Dialettica della forma di valore, ed. Riccardo Bellofiore and Tommaso Redolfi Riva, Editori Riuniti, Rome, 2009, p. 504.
[ 46 ]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sbegriffs bei Marx, p. 151.
[ 47 ] Ibid., p. 158.
[ 48 ] Karl Marx, 'The Commodity. Chapter One, Volume One,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Capital', in Albert Dragstedt, ed., Value: Studies by Karl Marx, New Park Publications, London, 1976, p. 20(中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第38页,翻译有改动——译注)。
[ 49 ]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sbegriffs bei Marx, pp. 163–4.
[ 50 ] Ibid., p. 165.
[ 51 ]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价格」是由劳动时间控制的,这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但这一点只有通过不断的偏差才会实现,这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竞争和技术变化导致的,而且是因为社会需求在将一定份额的社会劳动(即总的劳动)分派给各个别生产部门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52 ]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sbegriffs bei Marx, pp. 245–6.
[ 53 ] Ibid., p. 250.
[ 54 ] Backhaus, Dialektik der Wertform, p. 265.
[ 55 ]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mplete Works, vol. 43, Lawrence & Wishart eBook, p. 69(中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四卷第24页——译注)。
[ 56 ] 在下文中,像在Bellofiore, 'Lost in Translation: Once Again on the Marx–Hegel Connection'一文中一样,我们区分了拜物教性质和拜物教:「Fetischcharakter——资本主义社会实在所呈现的'对象性的'、物一般的、异化的性质——实际上是非常真实的:它是一个现象(Erscheinung)。而欺骗性的幻相或假相(Schein)在于将社会属性归于事物本身,当作它们的自然属性:后者就是Fetischismus,拜物教。但只有在资本的社会关系之外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现实中,依附在事物上的'社会属性'是非常实际的。」
[ 57 ] Backhaus, Dialektik der Wertform, p. 308.
[ 58 ] 本文的这一节代表的主要是其中一位作者的立场(里卡多·贝洛费奥雷)。
[ 59 ] 下面的论证大部分基于Bellofiore, 'Lost in Translation: Once Again on the Marx–Hegel Connection'和'Marx and the Monetary Foundations of Microeconomics', in Ricardo Bellofiore and Nicola Taylor, eds, The Constitution of Capital: Essays on Volume I of Marx's Capital, Palgrave Macmillan, Basingstoke, 2004。
[ 60 ] Roberto Fineschi, Ripartire da Marx, La città del sole, Naples, 2001中强调了有关尺度(measure)、标尺(measuring rod)和量度(measurement)的区分。
[ 61 ] Massimiliano Tomba, Marx‘s Temporalities, Brill, Leiden and Boston MA, 2012.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Philosophia 哲学社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scieok.cn/post/2985.html
-
<< 上一篇 下一篇 >>
新马克思阅读:如何将政治经济学重新引入社会批判理论中?
24232 人参与 2022年04月10日 21:58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