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在迄今为止的任何形式上都是不平等的。虽然马克思主义方法和女性主义分析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女性在这些社会中的地位都是必要的,但事实上女性主义一直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本文对「女性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作品都提出了挑战,并认为我们不得不对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结合进行严肃分析。我们希望这篇论文能如它所应当的那样,引起相当大的辩论。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婚姻」就像英国普通法中描绘的夫妻婚姻: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是一体的,这个一体即马克思主义。[^1] 最近试图整合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尝试对作为女性主义者的我们来说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将女性主义斗争纳入了反对资本的「更大的」斗争中。为了进一步继续我们的比喻,我们要么需要一段更健康的婚姻,要么我们就干脆离婚。 在这场婚姻中的不平等,就像大多数社会现象一样,并非偶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女性主义往最好了说也是不如阶级冲突重要的,往最坏了说就是工人阶级的分裂。这种政治立场产生了一种分析,将女性主义吸收到阶级斗争中。此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分析能力掩盖了它在性别歧视方面的局限性。我们将会在这篇文章提出,虽然马克思主义分析为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发展规律提供了必要的见解,但马克思主义的分类方式是完全忽视性别的。只有专门的女性主义分析才能揭示男女之间关系的系统特征。然而,女性主义的分析本身是不充分的,因为就目前看来它忽视历史,并且尚不是完全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特别是其历史和唯物主义的方法,以及女性主义的分析,特别是对父权制作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结构的认同,必须被放在一起分析,如果我们希望能够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其中女性的困境的话。本文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我们讨论的第一部分探讨了几种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女性问题」的解决方法。然后,在第二部分中我们转向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的作品。在注意到激进的女性主义对父权制定义的局限性之后,我们提出了我们自己的定义。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双方的优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妇女的现状都提出了建议。我们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女性主义的对象,纠正近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作品中的不平衡,并提出了一个对我们当前的社会经济构成的更完整的分析。我们认为,唯物主义分析表明,父权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东西,也是一种社会和经济结构。我们认为,一旦把我们的社会看作是以资本主义和父权方式组织的,它就可以被最完美地理解。在指出父权利益和资本主义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时,我们认为资本的积累既能适应父权社会结构,又有助于父权制的再生产。我们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在现在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这说明了一种父权制的社会关系最终支持资本主义的方式。简而言之,我们认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之间已经进化出了一种伙伴关系。 在最后部分,第四部分,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政治关系解释了在左翼对「女性问题」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对女性主义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要走向一种更加进步的联合,不仅需要我们提高对阶级和性关系的智力理解,也需要扭转当下左翼政治中的统治和从属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问题
「女性问题」从来都不是「女性主义的问题」。女性主义问题针对的是男女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即男性主导女性的原因。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对女性立场的分析都是女性与经济体系的关系,而不是女性与男性的关系,这显然假设了后者将会在对前者的讨论中得到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对女性问题的分析中有三种主要形式。所有这三种形式都能看到妇女的压迫与生产的联系(或缺乏联系)。在将妇女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同时,这些分析一致地将男女关系归入工人与资本的关系。首先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和列宁,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把所有妇女纳入工薪劳动力,也看到了这个过程推毁了劳动的性别分工。其次,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将女性纳入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分析。在这种观点中,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认为是再现了资本主义制度,而我们都是这个制度中的工人。第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关注家务劳动及其与资本的关系,一些人认为家务劳动产生剩余价值,于是家务工人直接为资本家工作。我们依次研究了这三种方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承认了妇女的地位低下,并将其归因于私有财产的制度。[^2] 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妇女必须为主人服务,践行一夫一妻制,并生产继承人来继承财产。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中,妇女没有受到压迫,因为没有可以传家的私有财产。恩格斯进一步认为,随着工薪劳动的扩大破坏了小规模的农民,妇女和儿童和男性一起被纳入工薪劳动力,结果是男性户主的权威被削弱,父权关系被毁灭。[^3] 对当时的恩格斯来说,妇女参与劳动力是她们解放的关键。资本主义将抹去性别差异,平等对待所有工人。妇女将在经济上独立于男人,也将与男人平等地参与无产阶级革命。革命之后,当所有人都是工人以及私有财产被废除时,妇女将从资本和男性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了对于女性来说参与劳动意味着的苦难,因为这导致女人同时有两份工作,家务和工薪工作。然而,他们强调的不是女性在家庭中的持续的从属地位,而是资本主义对父权关系的「侵蚀」的进步特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务劳动也将被集体化,从而减轻妇女的双重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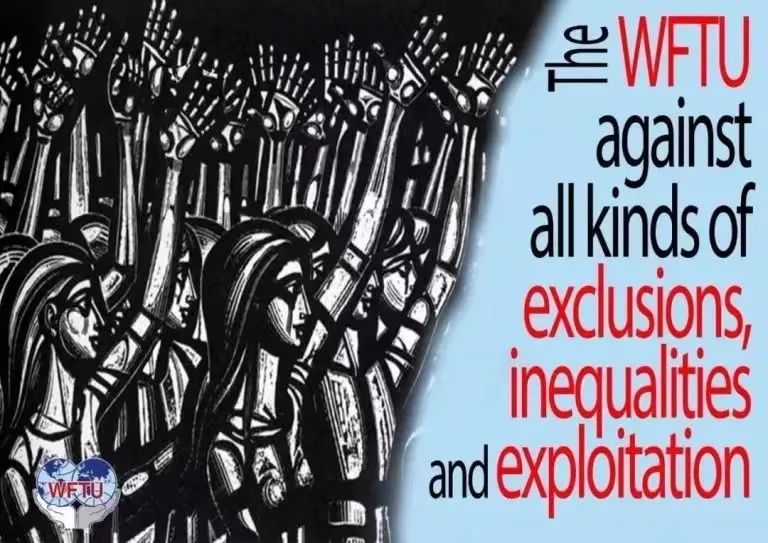
这第一种马克思主义方式的政治含义是明确的。妇女解放首先要求,妇女要成为像男人一样的工薪工人,其次,要求她们要与男人一起加入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和私有财产制是妇女受到压迫的原因,就像资本是所有工人被剥削的原因一样。 尽管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当时女性的悲惨处境,但他们没有关注资本主义统治下男女经历的差异。他们没有关注女性主义的问题 —— 女性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受到压迫的。因此,他们没有识别出男性从妇女持续的从属地位中获得的既得利益。就像我们第三部分说的,男性受益于不必做家务,受益于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的服务,受益于在劳动力市场中有更好的地位。父权制并不像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想象的那样,是返祖的残羹冷炙,会迅速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淘汰掉,相反,父权制不仅活下来了,还和资本主义一起繁荣了。由于资本和私有财产制不会造成对妇女的压迫,因此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并不会导致妇女压迫的终结。 也许最近最受欢迎的例证了第二种马克思主义方法(日常生活学派)的文章是伊莱·扎雷茨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发表的系列文章。[^4] 扎雷茨基同意女性主义的分析,他认为性别歧视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新现象,但他强调当今性别歧视的形式是由资本塑造的。他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下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经历。在恩格斯时代的一个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已然成熟,他指出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全部的女性纳入与男性平等的劳动力。相反,资本在家庭、家族和个人生活三者和工作场所之间创造了一种隔离。[^5] 扎雷茨基说,由于工薪工作和家庭工作之间的分离,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性别歧视变得更加致命。妇女日益增加的压迫是由于她们被排除在工薪工作之外。扎雷茨基认为,男人因为不得不做工薪工作而受到压迫,而女人却因为不被允许做工薪工作而受到压迫。妇女被排除在非农业劳动力之外主要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因为资本主义既创造额外的工薪工作,又要求妇女在家里工作,以便为资本主义制度复制工薪工人。女性复制劳动力,为工人提供心理照料,在异化的海洋中提供一个亲密的岛。在扎雷茨基看来,女性劳动是为了资本,而不是为了男性;就是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分离,以及资本主义带来的家务私有化,创造出了女性在家里私下为男人工作的感觉。女人为男人工作的外表和女人为资本工作的现实之间的区别,导致了对妇女运动能量的误导。女性应该认识到,女性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即使她们是在自己家工作。 在扎雷茨基看来,家庭主妇的出现和无产阶级一起,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典型劳动者,[^6] 对ta们生活的分割同时压迫着无产阶级丈夫和家庭主妇妻子。只有对「生产」的一种包括妇女在家里的工作和所有其他社会必要活动的重新概念化,才能使社会主义者努力建立一个克服这种破坏性的分离的社会。根据扎雷茨基的说法,男人和女人应该一起努力(或者各自努力)重新统一他们生活中被分裂的领域,创造一个人道的社会主义,满足我们所有的私人和公共需求。如果承认资本主义是ta们的问题的根源,男人和女人就会反对资本,而不是彼此。由于资本主义导致了我们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分离,资本主义的终结将结束这种分离,重新统一我们的生活,并结束对男人和女人的压迫。 扎雷茨基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女性主义运动,但他最终主张将该运动重新导向。扎雷茨基接受了女性主义的观点,即性别歧视早于资本主义就存在;他已经接受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论点,即家务工作对资本的再生产至关重要;他认识到家务是艰苦的工作,并没有贬低它;他使用了男性霸权和性别歧视的概念。但他的分析最终建立在分离的概念上,即建立在可以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名为分裂的概念之上,并把它当作问题的关键。就像20世纪早期的认为女性和男性的领域是互补的,分离的,但同样重要的互补球体论,扎雷茨基在很大程度上否认了性别不平等和男女不平等的影响。他关注的是女性、家庭和私人领域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此外,即便资本主义创造了正如扎雷斯基所说的私人领域,为什么女性在那里工作,而男性在劳动力中工作?当然,这一点不能通过不参照父权制来解释,即男性对女性的系统性主导地位。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劳动力市场、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不完全是男女之间的分工,而是那种使男性处于上级地位,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分工。 正如恩格斯将私有财产制看作资本主义对压迫妇女的一大贡献,扎雷茨基也这么看私人领域。因为妇女在家里私下劳动,所以她们受到压迫。扎雷斯基和恩格斯将前工业化时代的男性家庭和社区浪漫化了,在其中妇女、成人、儿童在以家庭为中心的企业中一起工作,所有人员参与社区生活。扎雷茨基的人道社会主义想要使家庭团聚,重建那个「快乐的作坊」。 虽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利益,但这完全不代表我们确定两者都在争取同一种人道社会主义,我们也不确定男人和女人对运动所需要的斗争有相同的概念,更不用说资本到底是不是我们当前受到压迫的唯一原因。尽管扎雷茨基认为女性看上去是为了男性工作,但实际上是为了资本,我们认为女性在家庭中的的确确是为男性工作 一一 尽管也复制了资本主义。重塑「生产」的概念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我们想要创造的社会,但在它被创造出来之前,男女之间的斗争必须和反对资本的斗争一起继续。 关注家务劳动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也把女性主义斗争纳入了反对资本的斗争中。玛丽亚罗萨·达利亚·科斯塔对家务劳动的理论分析本质上是关于家务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以及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而不是关于家务劳动中体现的男女关系。[^7] 然而,达利亚·科斯塔的政治立场,即妇女应该要求家务工资,极大地提高了对于妇女的家务劳动重要性的意识。这一需求在美国各地的妇女团体中直到现在都存在争议。[^8] 通过提出妇女不仅为资本复制劳动力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而且通过这项工作创造剩余价值,[^9] 达利亚·科斯塔也极大地提高了左派对家务劳动重要性的意识,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家务劳动与资本关系的长期争论。[^10] 达利亚·科斯塔利用女性主义对家务劳动作为真实劳动的理解,主张其在资本主义下的合法性,主张家务劳动应该获得工资。妇女应该声索家务劳动的工资,而不是允许自己被迫加入传统的劳动力,在那里,做「加倍劳动」的妇女仍然会免费为资本提供家务服务,同时还提供工薪劳动。达利亚·科斯塔建议,领取家务劳动工资的妇女们最好能够一起组织家务劳动,提供社区儿童护理、膳食准备等。要求领取工资以及领取工资本身提高了她们对实际工作重要性的意识;她们将看到它的社会意义,以及它的私人必要性,这是迈向更全面的社会变革的必要的第一步。 达利亚·科斯塔认为,家务劳动在社会意义上的重要性在于它对资本的必要性。妇女的战略重要性也以此为根据。通过要求家务劳动的工资和拒绝加入劳动力市场,妇女可以领导反对资本的斗争。妇女社区组织可以颠覆资本,不仅为抵抗资本的侵蚀奠定基础,而且还为一个新社会的形成奠定基础。 达利亚·科斯塔认识到,男子将抵制妇女解放(这将在妇女在社区组织起来时发生),妇女将不得不努力反对他们,但这场斗争是一场必须进行的辅助斗争,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对达利亚·科斯塔来说,妇女斗争是革命性的,不是因为她们是女性主义者,而是因为她们是反资本主义的。达利亚·科斯塔通过使妇女成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在妇女斗争革命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妇女因此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使妇女的政治活动合法化了。[^11] 
妇女运动从来没有怀疑过女性奋斗的重要性,因为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女性的解放是她们的目标,这只能通过女性的奋斗来实现。达利亚·科斯塔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家务劳动的社会本质,这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进步。但就像我们这里审视过的另外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她的关注点是资本而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男人和女人具有不同的利益、目标和策略这一事实,被她关于资本如何让我们全都吃瘪以及女性工作在其中的重要性的强力论证给遮蔽了。女性主义的修辞出现在达利亚·科斯塔的作品中(对女性的压迫,与男性的斗争),但女性主义的关注焦点却没有出现。如果是这样的话,达利亚·科斯塔可能会说,家务劳动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在于它在延续男性霸权方面的关键作用。女人做家务,为男人做劳动,对维持父权制至关重要。 恩格斯、扎雷茨基和达利亚·科斯塔都没有充分分析家庭内部的劳动过程。谁能从妇女的劳动中受益?当然是资本家,也肯定是男人,他们作为丈夫和父亲在家里得到个性化的服务。这些服务的内容和范围可能因阶级或族群而异,但他们受到服务的事实却全都相同。在奢侈消费、休闲时间和个性化服务方面,男性的生活水平都高于女性。[^12] 唯物主义的方法不应该忽视这一关键点。[^13] 由此可见,男性对女性持续的压迫有物质利益。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虚假的意识」,因为大多数男人都可以从废除父权制及其等级制度中受益。但在短期内,这[父权制] 等于一种对ta人劳动的控制权,而男性是不会轻易地自愿放弃它的。 虽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忽视了家务劳动,强调女性参与劳动力,但最近的两种做法都太过强调家务劳动以致于忽视了女性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然而,这三者都试图将妇女纳入工人阶级的范畴,并将妇女的压迫视为阶级压迫的一个方面。这样做导致所有人都忽视了女性主义分析的对象 —— 男女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的问题被精致地分析了,但它们也被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焦点一直是阶级关系;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对象一直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虽然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方法可以用来制定女性主义策略,但上面讨论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方法显然没有这样做: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明显主导着他们的女性主义。 正如我们已经提出的,这部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分析威力。马克思主义是关于阶级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过程、阶级支配地位的再生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的一种理论。资本主义社会是由积累过程的需求所驱动的,最简洁的总结为生产是面向交换的、而不是使用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只有在它有助于创造利润时才很重要,而产品的使用价值则只是一个偶然的考虑。利润来自资本家利用劳动力的能力,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低于他们创造的价值。利润的积累过程改变了生产的关系,同时系统性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劳动力的剩余,大量人口的贫因和更多人口的近乎贫困,这些人类对资本的指责是资本积累过程本身的副产品。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可以「无忧地留给他们自己」。[^14] 与此同时,资本创造了一种意识形态,它随资本一起成长,即个人主义、竞争、统治,以及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特定的消费主义。无论一个人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是什么,他都必须承认这些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使我们能够了解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东西:生产的结构、特定职业结构的产生,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是一种「空空的萝卜坑」的发展理论。例如,马克思预测了无产阶级的增长和小资产阶级的灭亡。更精确、更详细地,布拉维米等人解释了「萝卜坑」的创造,例如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书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的出现。[^15] 正如资本创造的这些「萝卜坑」对填充其中的个体们不作区分一样,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范畴,「阶级」「剩余劳动力」「工薪劳动者」,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是特定的人占据特定的萝卜坑。他们没有给出线索来解释为什么女性在家庭内外都服从于男人,而不是反过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就像资本本身一样,都是性别盲目的。马克思主义的分类方式不能告诉我们谁将会填补「空空的萝卜坑」。马克思主义对女性问题的分析,在这一基本问题上面已经吃尽苦头。
走向更有用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社会分析的方法,是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朱丽叶·米切尔和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女权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出了新的方向。我们赞同米切尔说的: [^17] 社会主义和「我们的关系」从来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应该是使用科学社会主义[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方法] 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我们的压迫的具体性质,进而分析我们的革命角色。我相信,这种方法需要理解激进的女性主义,就像理解过去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理论们一样。[^16]
正如恩格斯所写的: 根据唯物主义的概念,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是直接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这又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生存手段的生产,例如食物、衣服、住所和生产所需的工具;另一方面,是人类本身的生产,物种的繁殖。某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人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是由这两种生产方式所决定的……[^17]
这就是米切尔尝试过的那种分析。在她的第一篇文章《女人:最漫长的革命》中,米切尔同时研究了市场工作以及生殖、性行为和养育孩子的工作。[^18] 米切尔并没有完全成功,也许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女性的工作对她来说都算作生产。只有市场工作被确定为生产;妇女工作的其他领域(被松散地统称为家庭)被确定为意识形态的。很大程度上组织了生殖、性行为和育儿活动的父权制,对米切尔来说没有物质基础。《女性地位(Women's Estate)》是米切尔对她第一篇文章的扩展,更关注于女性在市场工作的分析,而不是女性在家庭中工作的分析。这本书关注女性与资本的关系多于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关注女性为资本工作的问题多于女性为男性工作;更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不是激进女性主义的影响。在她后来的作品《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中,米切尔探索了研究男女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女性和男性形成不同的、基于性别的个性。[^19] 米切尔似乎在说,父权制在心理领域的作用非常大,使得女性和男性儿童学习着成为父权制意义上的标准女性和标准男性。在这里,米切尔关注的是她最初轻视的领域,生殖、性行为和养育孩子,但由于她将它们放在意识形态领域,她还是继承了自己早期分析的根本弱点。她清楚地把父权制描述为基本的意识形态结构,就像资本是基本的经济结构那样: 简单地说…我们正在…处理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和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模式。^20
尽管米切尔讨论了他们的相互渗透,她没有在女性和男性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中给予父权制一个物质基础,她也类似地没有注意到人格形成和性别创造过程的物质方面原因,这限制了她的分析的实用性。 舒拉米思·费尔斯通将唯物主义分析引入父权制,连接了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21] 她对唯物主义分析的使用并不像米切尔的那样矛盾。她认为性的辩证法是基本的历史辩证法,而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女性繁殖人类物种的工作。费尔斯通利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女性的地位,主张父权制存在一种物质基础,这些作品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但它过分强调了生物学和繁殖活动。我们需要理解的是,性(一种生物学事实)是如何变成性别(一种社会现象)的。有必要将妇女的所有类型的工作都放在其社会和历史背景下,而不是只关注生殖这一项。虽然费尔斯通的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用法,但是她坚持将男性对女性的主导地位作为所有其他压迫(阶级、年龄、种族)的基石,这表明她的书应该更恰当地被归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她的作品仍然是对激进女性主义立场的最完整的陈述。 费尔斯通的书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们非常轻松地驳回了。例如,扎雷茨基称之为「对主观性的要求」。然而,费尔斯通的这本书让女性兴奋的是她对于男性对女性的权力的分析,以及她对这种情况的非常合理的愤怒。她关于爱的一章曾经是我们理解爱的核心方式,现在仍然如此。这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处理的(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一个「男性意识形态」,而是对男人压迫女人的客观后果的一种阐释,它让人有生活在父权制下的感觉。「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并不像扎雷茨基说的那样,是一种对主观性和更好的感受的请求:这是一种要把男性的权力和女性的从属地位当做一种社会和政治现实来承认的要求。 
父权制与激进女性主义
激进女性主义的写作的主要目的是记录「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一口号。她们认为,女性的不满并不是出于适应不良者的神经质的衰叹,而是对这个女性被系统地支配、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结构的反应。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中产阶级婚姻中以男性为中心的情感结构、女性在广告中的运用、把女性心理当做神经质的所谓理解 —— 女性的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被从头到脚地研究过了。激进女性主义文学的体量太庞大了,没办法简单概括。但同时,它在聚焦心理学这一点上是从一而终的。纽约激进女性主义者的章程是「自我的政治」。对于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来说,「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意味着,最初的基本阶级划分是性别之间的划分,历史的动力是男性对权力和统治女性的争取,这就是性的辩证法。[^22] 因此,费尔斯通改写了弗洛伊德,以理解男孩和女孩在权力的意义上发展成男人和女人。[^23] 她对「男性」和「女性」性格痕迹的描述是典型的激进女性主义笔法。男性寻求权力和统治;他的气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竞争的和务实的;根据费尔斯通的说法,男性意味着「技术模式」。女性的气质是供养者,是艺术的和哲学的,可以概括为「审美模式」。 毫无疑问,「审美模式」是女性的想法会让古希腊人感到相当震惊。这里就是激进女性主义分析的错误之处:激进女性主义者提出的「性的辩证法」将「男性」和「女性」仅在当下表现出来的那些性格特点投射到了所有历史之中。激进女性主义的分析就理解当下来说,有极强的说服力。它最大的弱点是过于关注心理学方面的东西,以至于忽视了历史。 其原因不仅在于激进女性主义的方法,还在于父权制的本质 —— 一种具有惊人弹性的社会组织形式。激进女性主义者用「父权制」来指代一种以男性主导女性为特征的社会制度。凯特·米勒的定义很经典: 我们的社会…是父权制的。如果人们回忆起军事、工业、技术、大学、科学、政治办公室、金融力量——简单来说,社会内的每一个权力途径,包括警察的强制力,都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事实就显而易见了。[^24]

这种激进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定义适用于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社会,它们在这一点上都高度相似。激进女性主义者对历史的使用通常仅限于提供父权制在任何时间和地方都存在的例子。[^25] 对于在妇女运动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和主流社会科学家来说,父权制指的是一种男人之间的关系制度,它形成了封建社会和一些前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轮廊,在其中社会等级取决于与生俱来的一些东西[译者注:父权制Patriarchy有宗法制、家父长制的含义] 。资本主义社会被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理解为精英主义\绩效至上、官僚主义和非个体化/客观冷漠的(impersonal);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阶级统治的制度。[^26] 对于这两种社会科学家来说,无论是历史上的父权社会还是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都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男性之间的使他们能够支配女性的关系系统。
定义父权制 我们可以有效地将父权制定义为男性之间的一套社会关系,它有物质基础,虽然等级分明,但还是在男性之间建立了相互依赖和团结,这也使他们能够支配女性。虽然父权制是等级化的,不同阶级、种族或民族的男性在父权制中有不同的地位,但他们在对各自的女人的共同统治关系中也是团结起来的;他们相互依赖来维持这种统治。等级制度「能起作用」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在现状中创造了既得利益。那些地位较高的人可以「收买」那些地位较低的人,通过一种给予他们能够凌驾于其他地位更低的人的权力的方式。在父权制的等级制度中,所有的男人都被这样收买了。因为无论他们的地位如何,他们总归至少能够凌驾于一些女人之上。有一些证据表明,当父权制第一次在国家社会中制度化的时候,想要上位的统治者许诺男人们在字面意义上成为他们的家庭的首领(也就是加强他们对妻子和孩子的控制),以换取男人们将他们的一些部落资源割让给新的统治者。[^27] 男人互相依赖(尽管他们的地位不同)来维持对女性的控制。 父权制所建立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在于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控制。男子通过禁止妇女获得一些基本的生产资源(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支付生活工薪的工作)和限制妇女的性取向来维持这种控制。[^28] 一夫一妻制的异性婚姻是一种相对较新和有效的形式,似乎可以让男性同时控制上述两个领域。控制妇女的资源获取能力和她们的性取向,反过来使男性能够控制妇女的劳动力。这种控制既以为男性提供许多个人的和性方面的服务为目的,也以抚养孩子为目的。女性为男性提供的服务,使男性不必做许多不愉快的任务(比如打扫厕所),既发生在家庭的外部也发生在家庭的内部。家庭之外的例子包括男老板和教授对女员工和学生的骚扰,以及通常使用秘书来跑腿、煮咖啡和提供一种「性感」的氛围。然而,抚养孩子(无论孩子的劳动力是否对父亲直接有利)是延续父权制制度的一项关键任务。正如阶级社会必须被学校、工作场所、消费规范等复制一样,父权制的社会关系也必须被复制。在我们的社会中,儿童通常是由妇女在家里抚养的,这些妇女恰恰是在社会中被定义、看作不如男人的,而男人却很少出现在家庭场景中。以这种方式长大的孩子通常能很好地领悟到他们自己在性别等级制度中所属的地位。然而,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家庭以外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一系列父权行为被教导,妇女的劣势地位被强加和巩固:教堂、学校、体育、俱乐部、工会、军队、工厂、办公室、保健中心、媒体等等。 因此,父权制的物质基础并不在于家庭中的养育孩子的行为,而是在于所有使男性能够控制女性劳动的社会结构。使得父权制生生不息的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在理论上是可识别的,也是可与其他方面分离的。盖尔·鲁宾通过确认「性/性别体系」,极大地提高了我们识别这些社会结构中的父权制元素的能力: 「性/性别系统」是指社会将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物的一套系统。在其中,这些被转化过后的性需求得到了满足。[^29]
我们生来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雄性和雌性,但我们是被后天塑造成为社会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恩格斯所说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方面解释了我们是如何被这样塑造的:「人类自身的生产,种群的繁殖。」 社会决定了人类如何繁殖他自身这个种群。例如,如果人在生物学上是多性别的,那么繁殖将是偶然的。按性别划分的严格的劳动分工是所有已知社会都共有的一种发明,它创造了两种相互独立的性别,以及一种让男性和女性出于经济原因聚在一起的需求。于是,它有助于将他们性需求的满足导向异性恋。虽然从理论上讲,性劳动分配不应该包含着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但在大多数已知的社会中,社会上按性别划分的劳动分工都是给予妇女更低的工作地位的。性别分工也是性别亚文化的基础,在这些亚文化中,男性和女性的生活体验不同:男性权力的物质基础(在我们的社会中)不仅使得他们可以不做家务,可以获得更好的就业,而且也体现在心理的方面。 人们如何满足他们的性需求,如何繁殖,如何向新一代灌输社会规范,如何学习性别,作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感觉 一一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鲁宾称为性/性别系统的领域。鲁宾强调了亲属关系(它的影响会告诉你,你可以与谁一起满足性需求),以及通过育儿和「恋母机器」发展出来的具有性别特征的人格。此外,我们还可以使用性/性别系统的概念来检查所有其他社会机构在定义和加强性别等级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鲁宾指出,从理论上说,一个性/性别系统可以是女性主导、男性主导或平等主义的,但鲁宾拒绝给各种已知的性/性别制度贴上标签,或以此种方式划分历史时期。我们之所以把我们现在的性/性别体系标记为父权制,是因为它怡当地捕捉到了等级制度和男性主导地位的概念,我们认为这是当前制度的核心。 经济生产(马克思主义者习惯将它称为生产方式)和性/性别领域的人的生产都决定了恩格斯所说的「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国家的人民赖以生活的社会组织」。因此,只能通过观察人与物的生产和再生产来理解整个社会。[^30] 没有所谓的「纯粹的资本主义」,也不存在「纯粹的父权制」,因为它们必须共存。存在的是父权资本主义,或父权封建主义,或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社会,或母系园艺 (horticultural) 社会,或父系园艺社会,等等。在生产的一个方面的变化和另一个方面的变化之间似乎没有必要的联系。例如,一个社会可以经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保持父权制。[^31] 然而,常识、历史和我们的经验都会告诉我们,生产的这两个方面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其中一个方面的变化通常会在另一个方面产生运动、紧张或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种族等级也可以被理解。随着对「肤色/种族系统」的定义,进一步的阐述也就是可能的。「肤色/种族系统」指的是一个将生物学意义上的肤色转变为社会意义上的种族的社会生活竞技场。种族等级制度,就像性别等级制度一样,是我们社会组织的一个方面,也是人们如何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方面。它们根本不是意识形态的;它们构成了我们生产方式的第二个方面,即人的生产和再生产。那么,最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不要把我们的社会简单地称为「资本主义的」,而应该说是「父权资本白人至上主义的」。在后面的第三部分,我们说明了资本主义适应和利用种族秩序的一种形式,以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相互关系的几个例子。 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工人的等级制度创造了场所,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类方式不能告诉我们谁将填补哪些场所。性别和种族等级制度决定了谁填补空缺场所。父权制不是简单的等级组织,而是特定的人填补特定的场所的等级制度。研究父权制,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是女性被统治以及如何被统治。虽然我们认为大多数已知的社会都是父权制的,但我们并不认为父权制是一种普遍的、不变的现象。相反,父权制作为一种允许男性支配女性的男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形式和强度上都发生了变化。研究在历史上的社会中男性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其支配女性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研究男人之间的等级制度和他们获得父权利益的机会的区别也至关重要!当然,阶级、种族、国籍,甚至婚姻状况和性取向,以及明显的年龄,都在这里发挥作用。不同阶层、种族、国家、婚姻状况或不同性取向群体的女性对抗着不同程度的父权制力量。女人们自己也可能对在父权等级制中地位低于她们的男性亲属们的其他男性行使着阶级、种族或国家权力,甚至父权权力(通过她们的家庭关系)。 概括地说,我们将父权制定义为一套具有物质基础的社会关系,在其中男性之间存在等级关系,也存在不同等级之间的团结,使他们能够支配妇女。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性对女性的劳动力的控制。这种控制通过拒绝妇女获取必要的有经济效益的生产资料和限制妇女的性取向来维持。男人行使权力,接受女性的私人服务,不用做家务或抚养孩子,有权为了性而使用女性的身体,在感觉上和现实中都是强势的。我们目前所经历的父权制的关键因素是:异性恋婚姻(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性恋恐惧症),女性养育子女和做家务,妇女对男性的经济依赖(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安排来执行),国家,以及许多基于男性之间社会关系的机构:体育、工会、行会、大学、教堂、公司和军队。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父权制的资本主义,所有这些因素都需要被仔细分析。 男性之间的等级制度和相互依赖以及女性的从属地位是我们社会运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些关系是系统性的。抛开建立这些关系的问题不说,我们要问,我们能够识别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父权关系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必须发现男人和男人之间存在这种父权制的关系。尽管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都声称这种关系不再存在,或者,即便存在也最多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残余物。我们能理解人类之间的这些关系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延续下去的吗?我们能确定父权制塑造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方式吗? 
父权制与资本的伙伴关系 我们怎么识别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父权社会关系?似乎每个女人都只受到自己的男人的压迫;她的压迫似乎是一件私人的事。男人之间的关系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似乎都是分散的。我们很难把男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看作系统的父权制。然而,我们认为,父权制作为一种男女关系体系存在于资本主义中,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父权制和资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健康而强大的伙伴关系。然而,如果人们从父权制的概念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开始,人们就会立即认识到父权制和资本的伙伴关系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男人和资本家经常有利益冲突,特别是在妇女的劳动力的使用上。这种冲突可能体现出来的一种方式是:绝大多数男性可能希望他们的女人在家里亲自为他们服务。少数男性是资本家,他们可能希望大多数女性(不是自己的)在工薪劳动力市场工作。在研究这场关于女性劳动力权力的冲突的紧张关系时,我们将能够确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父权关系的物质基础,以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之间伙伴关系的基础。
工业化与家庭工资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从他们在19世纪所目睹的一些社会现象中做出了相当合乎逻辑的推论。但他们最终低估了刚起步的资本需要与之对抗的先前存在的父权社会之力量,以及对资本进行调整以适应这些力量的需求。工业革命吸引了所有的劳动力,包括妇女和儿童;事实上,第一批工厂几乎只使用儿童和女性劳动。[^32] 妇女和儿童可以独立于男人来挣工资,这既破坏了权威关系(如上文第一部分所讨论的),又使所有人的工资都保持在低水平。考茨基在1892年如此描述了这个过程: 然后,随着工人的妻子和孩子…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男性工人的工资可以安全地降低到仅满足他自己的个人需求的水平,而不会有停止新劳动力供应的风险。
此外,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提供了额外的优势,因为她们不具有男人那样的抵抗能力:她们进入工人队伍,极大地增加了市场上出售的劳动力数量。
因此,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也降低了男性工人的抵抗能力,因为他们在市场上是过剩的;由于这两种情况,它降低了男性工人的工资。[^33]
低工资和强迫所有家庭成员参与劳动力大军对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可怕影响被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了。考茨基写道: 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破坏工人的单一家庭,而是夺走它所有的一切,除了它的那些令人不快的特征。今天妇女在工业化工作中的活动…意味着她在既有的负担上又多了新的一个。但一个人不能服务两个主人。每当工人的妻子必须帮忙挣到每天的口粮时,他的家庭就难过了。[^34]
工人和考茨基都认识到女人参与工薪劳动的缺点。女人不仅是「更廉价的竞争者」,而且职业女性不是别人,就是他们自己的妻子,她们没办法很好地「服务于两个主人」。 男性工人抵制妇女和儿童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试图将她们排除在工会成员和劳动力大军之外。在1846年,《十小时倡议》声明: 不言自明的是,所有试图改善女工厂工人的道德和身体状况的努力都将会失败,除非她们的工作时间大大减少。的确,我们甚至可以说,已婚的女性最好专注于家务劳动,这比在工厂里跟着永不停歇的机器来劳动要好得多。因此,我们希望很快有一天,丈夫能够养活妻子和家人,而不用派前者去忍受棉纺厂的苦工事。[^35]
1854年,在美国,全国印刷工会决定不「通过法案 (act) 鼓励雇佣女性设计师」。男性工会成员不想为女工提供工会保护;而是试图把她们排除在外。1879年,雪茄制造商国际联盟主席阿道夫·斯特拉瑟说:「我们不能把女性赶出这个行业,但我们可以通过工厂法律来限制她们的日常劳动配额。」[^36] 虽然廉价竞争的问题可以通过适当安排劳动妇女和青年来解决,但扰乱家庭生活的问题却没办法这样解决。男性为男性保留了工会的保护,并要求建立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法。[^37] 保护性的劳动法虽然可能改善了一些对女性和童工最严重的虐待,但也限制了成年女性在许多「男性」工作中的参与度。[^38] 男人们试图将高工资的工作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想要提高男性的整体的工资水平。他们要求工资要高到足够用他们自己的工薪劳动来养活家庭成员。这种「家庭工资」制度逐渐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成为稳定的工人阶级家庭的规范。[^39] 一些观察人士声称,不上班的全职妻子是男性工人生活水平的一部分。[^40] 男性工人不是为男女平等的工资而战,而是寻求「家庭工资」;希望保留妻子在家里的服务。在没有父权制的情况下,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可能会直面资本主义,但父权社会关系分裂了工人阶级,允许一部分(男人)因拿取另一部分(女人)的利益而被收买。男人之间的等级制度和他们之间的团结在这个解决过程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家庭工薪」可以理解为解决当时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利益之间在妇女劳动力方面的冲突的一种方式。 
大多数成年男性的家庭工资意味着男性的妥协和共谋。它意味着其他人的低工资,例如年轻人、女性和社会定义的低等男性(爱尔兰人、黑人,等等父权阶层中最低的群体,他们被剥夺了许多父权福利)。妇女、儿童和低等男子的低工资由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隔离来执行,进而由工会和管理机构以及学校、培训项目甚至家庭等辅助机构来维持。工作的性别隔离,通过确保妇女拥有较低收入的工作,既保证了妇女对男子的经济依赖,又加强了妇女和男子分别适合不同领域的无形观念。因此,对大多数男性来说,家庭工资的发展从两方面保障了男性统治的物质基础。首先,女性的工资水平低于男性。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低工资,使男性对比女性的物质优势得以延续,并鼓励女性选择全职太太作为职业。其次,女性在家里做家务,做其他直接使男性受益的服务。[^41] 妇女的家庭责任反过来又加强了她们低下的劳动力市场地位。[^42] 能看出来,在20世纪早期发展起来的这种解决办法,既有利于资本的利益也有利于父权制的利益。人们经常认为,资本家们认识到,在19世纪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盛行的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工人阶级家庭无法充分地自我繁殖。他们意识到,家庭主妇比有工资的妻子更能够生产和维持健康的工人,受过教育的孩子比未受过教育的孩子更能成为好的工人。这种交易包括向男性支付家庭工资,让女性留在家里。这既让当时的资本家满意,也让男性工人满意。尽管交易的条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直到今天,家庭以及女人在家庭中的劳动仍然还是通过提供一个劳动力的方式来服务资本,并且通过成为男性驰骋特权的空间来服务男人。女人们不仅努力服务着男人们和她们的家人们,也作为消费者服务资本。[^43] 家庭也是学习支配和服从的地方,正如费尔斯通、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许多人所解释过的那样。[^44] 顺从的孩子成为顺从的工人;女孩和男孩各自习得适当的角色。 虽然家庭工资表明资本主义在适应父权制,但儿童地位的变化却表明父权制在适应资本。孩子们和妇女一样开始被排除在工薪劳动之外。随着孩子们赚钱能力的下降,他们与父母的法律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美国工业时代的开始,满足孩子们对父亲的需求被认为对他们的幸福发展至关重要,甚至是首要的:在有争议的监护权案件中,父亲们享有法律优先权。布朗的研究表明,随着孩子为家庭经济福祉做出贡献的能力下降,母亲越来越被视为孩子幸福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在监护权有争议的案件中逐渐获得了法律优先权。[^45] 在这里,父权制适应了儿童不断变化的经济角色:当孩子有生产力时,男人声称拥有他们;当孩子变得无生产力时,他们就被发配给妇女。
二十世纪的伙伴关系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父权制将在资本主义把所有人都无产阶级化的需要面前枯萎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他们不仅低估了父权制的力量和灵活性,还高估了资本的力量。他们设想,撕裂封建关系的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力量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性的力量时,当代的观察者更好地看到了「纯粹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实际的」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区别。关于资本和种族秩序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讨论,提供了「纯粹」资本主义力量如何与历史现实相妥协的额外例子。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灵活性。 研究过南非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尽管种族秩序可能不允许每个人实行平等的无产阶级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障碍阻碍了资本积累。[^46] 抽象来说,分析师可能会讨论哪种安排可以允许资本家攫取最多的剩余价值。然而,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况下,资本家必须关注社会控制、工人群体的抵抗和工会的干预,以及国家的干预。为了让整个社会可持续,国家可能会干预;国家有必要监管一些资本家,以克服那些最极端的资本主义倾向。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那么资本家最大化了最大的实际利润。如果出于社会控制的目的,资本家以特定的方式组织工作,资本本身并不能决定谁(即哪些个人具有归属特征)在工薪劳动力中占据较高阶层,谁占据较低阶层。当然,这有助于让资本家本身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同样也可能是种族主义者(和性别歧视者)。资本主义既继承了主导群体的与生俱来的特征,也继承了从属群体的。 最近关于垄断资本创造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趋势的争论与这一理解是一致的。[^47] 资本家故意分割劳动力,使用一些与生俱来的特征来划分工人阶级,这显然源于对社会控制的需求,而不是狭义上的资本积累所必要的事情。[^48] 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不是所有这些分裂的尝试都能成功(在分裂方面),或者有利可图。资本塑造劳动力的能力取决于狭义上的资本积累的要求(例如,生产的组织方式是否需要大量工人之间的沟通?如果是这样,他们最好都说英语)[^49] ,也取决于一个社会内部的可能鼓励或强制资本去适应社会自身的力量(在南非给白人和黑人分别设置单独的洗浴间对于资本家来说,只能被理解为一个经济成本,但它低于试图迫使南非白人与黑人一起洗澡的社会成本)。 如果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争论的第一个要素是资本不是全能的,那么第二个要素就是资本是非常灵活的。资本积累遇到了预先存在的社会形式,既摧毁它们,又适应它们。资本的「适应」可以被视为这些旧有形式在新环境中冥顽不灵的力量的反映。即使他们坚持下去,他们也不是没有改变的。比如今天对种族和性别的意识形态理解,就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对种族和性别区分的强化之中形成的。
今天的家庭和家庭工资 我们在上面已经论证,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适应或相互适应,在20世纪早期以家庭工资的发展为形式。家庭工资巩固了父权制和资本之间的伙伴关系。尽管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有所增加,但我们认为,家庭工资仍然是当前性别分工的基石 一一 在这个分工中,女性主要负责家务,男性主要负责工薪工作。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较低的工资(再加上需要有人抚养孩子)保证了家庭作为一个必要的收入集中单位的存续。因此,由家庭工资支持的家庭便允许男人在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控制妇女的劳动。 虽然职业女性的增加可能会给家庭造成压力(类似于考茨基和恩格斯19世纪所指出的压力),但认为家庭的概念和现实以及性别分工很快就会因此消失是错误的。性别分工再次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妇女从事女性的工作,通常和她们曾经在家庭内部做的工作一样 —— 准备食物和服务,各种清洁,照顾人,等等。由于这些工作地位低工资低,父权关系仍然是完好的,尽管它们的物质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从家庭转移到工资差异。例如,卡罗尔·布朗认为,在资本主义内部,我们正在从「以家庭为基础」的父权制转向「以工业为基础」的父权制。[^50] 以工业为基础的父权关系以各种方式得到执行。为女性明确规定了较低的工资、较低的福利和较少的晋升机会的工会合同,不仅仅是返祖的宿醉一一即性别歧视态度或男性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情形 —— 它们其实维持着父权制度的物质基础。虽然有些人认为父权制已经在家庭中消失(例如,参看斯图尔特·伊文,《资本的意识》[^51] ),但我们不会这样认为。虽然资本和父权制之间妥协的条款随着以前位于家庭中的额外任务资本化而改变,并且女性的劳动力权力的部署的场所也在变化,[^52] 然而,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劳动力市场上极端的工作隔离所造成的工资差异,通过鼓励妇女结婚,加强了家庭,也加强了家庭劳动分工。家庭工资的「理想」 —— 一个男人可以挣到足够的钱来养活整个家庭——可能会让位于一种新的理想,即男人和女人都通过工资收入来贡献整个家庭的现金收入。因此,为了延续父权制,即男性对女性劳动力权力的控制,工资差异将变得越来越必要。工资差别将有助于将妇女的工作定义为比男子次要的工作,因为它需要妇女实际上继续以经济方式依赖男子。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地方的性别分工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父权制使自身得以延续下去的表现方式。 许多人认为,尽管资本和父权制之间的伙伴关系现在己经存在,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最终会无法容忍它;资本最终可能会摧毁家庭关系和父权制。论点的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家庭不是它的例子)倾向于普遍化,随着女性越来越能赚钱她们将越来越拒绝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并且因为家庭尤其压迫妇女和儿童,一旦人们可以自己靠自己生活它就会崩溃。 
我们不认为家庭中体现的父权关系如此容易被资本摧毁,我们也几乎没有看到什么证据表明这个家庭制度目前正在解体。尽管妇女劳动力参与率的增加使离婚更加可行,但离婚的动机对妇女来说并不是压倒性的。妇女的工资水平只能让少到几乎没有的一些妇女有能力独立和充分地养活自己和抚养孩子。传统家庭衰败的证据怎么说也是微弱的。离婚率并没有那么大幅度的增加,而是在各阶级中保持平稳;此外,再婚率也很高。直到1970年的人口普查,初婚率一直在历史性下降。自1970年以来,人们似乎一直在推迟结婚和生育,但最近,出生率已开始再次回升。现在的确有更大比例的人口生活在传统家庭之外。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正在离开他们父母的家,并且在他们结婚建立传统的家庭之前就开始自立门户。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女性,在子女长大后,经历配偶分居或死亡后,她们在自己的家庭中经历着孤独。然而,这些趋势表明,新一代的年轻人将在他们成年后的某个时候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高的比例形成核心家庭。1930年以来出生的群体最终结婚率和生育率比以前的群体要高得多。结婚和育儿的持续时间可能正在缩短,但其影响的范围仍在蔓延。[^53] 资本「摧毁」家庭的观点也忽视了使家庭生活具有吸引力的社会力量。尽管有人批评核心家庭对心理造成破坏,但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家庭仍然满足了许多人的真实需求。这不仅适用于长期的一夫一妻制,对抚养孩子的需求更是如此。单亲父母同时承受着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负担。特别是对工人阶级妇女来说,这些负担使劳动力参与的「独立」变得虚幻。单亲家庭最近被政策分析人士视为过渡性家庭结构,在再婚后成为双亲家庭。[^54] 女性劳动力参与增加的影响可能是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的减弱,而不是更频繁的离婚,不过这也缺乏证据。这几年关于谁做家务的统计数据,即使是妻子有收入的家庭也没什么变化:女性仍然做大部分的家务。[^55] 「一天当作两天用」对职业女性来说就是现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家庭之外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工,使女性在经济上依赖男性,即便她们自己也挣工资。然而,父权制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家庭关系的未来。因为父权制,就像资本一样,可以具有惊人的灵活和适应性。 无论家庭内部和其他地方的父权制劳动分工,是否对于资本来说「最终」是无法容忍的,它反正现在在塑造着资本主义。正如我们下面所说明的,父权制既使资本主义控制合法化,又使某些形式的资本斗争合法化。
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 父权制通过在男性之间建立和合法化的等级制度(通过允许所有等级的男性控制至少一些女性),加强了资本主义的控制,而资本主义价值观塑造了父权制下善的定义。 费尔斯通定义的心理现象就是在依赖和支配关系中发生之事的独到例子。它们出自男性社会权力的现实 —— 而女性没有权力 —— 但它们是由它们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的事实所塑造的。[^56] 如果我们用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来审视男性的性格特点 —— 竞争性的,理性主义的,支配的 —— 它们很像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描述。 这种「巧合」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首先,男人,作为工薪劳动者,在工作中被吸收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被驱使进入这些关系所规定的竞争中,并吸收相应的价值观。[^57] 激进的女性主义对男性的描述并没有完全超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第二,即使男人和女人实际上并没有按照性规范所规定的方式行事,男人也会为自己主张那些在主导意识形态中被重视的特征。于是举个例子,《克雷斯伍德高地》的作者发现,当男性是专业人士,整天操纵下属(通常使用基本的非理性的动机来训导出他们想要的行为)时,男性和女性将男性描述为「理性和务实的」。当妇女投入大量精力研究抚养儿童和儿童发展的科学方法时,《克雷斯伍德高地》里的男性和女性将妇女描述为「非理性和动感情的」。[^58] 这不仅有助于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男性」和「女性」的性格特征,而且也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正如女性的工作具有延续男性统治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双重目的一样,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也具有双重目的,即美化男性特征/资本主义价值观,以及诋毁女性的性格特征/社会需求。如果女性在其他的社会中是低级的或无力的,那么男性这样做的理由就和资本主义社会不一样了。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将女性贬低为感性的或非理性的才有意义。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将女性视为「依赖者 (dependent)」才有意义。「依赖者」的封号在封建社会中没有意义。由于分工确保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关心使用价值的生产,对这些活动的诋毁既掩盖了资本无法满足社会层面上决定性的需求,同时也在男性眼中贬低了女性,为男性占主导地位提供了理由。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可以从电视购物广告特有的矛盾心理中看出。一方面,他们致力于解决满足社会需求的真实障碍:(消灭)破坏衣服和刺激皮肤的洗涤剂,各种各样的劣质产品;另一方面,必须诋毁对这些问题的关切;这是通过嘲笑妇女即必须处理这些问题的工人来实现的。 一个证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伙伴关系的平行论点可能是关于劳动力中的性别劳动分工。性别分工的存在使女性从事低薪工作,并从事被认为适合女性角色的工作。妇女阶层是教师、慈善工作者和卫生保健领域的绝大多数。妇女在这些工作中所扮演的养育者角色地位很低,部分原因是男人诋毁妇女的工作。这些工作的地位很低,也因为资本主义强调个人独立和私营企业满足社会需要的能力,而这些重点与对集体提供社会服务的需要相矛盾。只要可以用它们是女人干的活儿来诋毁养育任务的社会重要性,就可以避免资本对交换价值的优先地位与【社会】对使用价值的需求之间的对抗。这样,就不是女性主义,而是分裂工人阶级的性别歧视削弱了工人阶级。 
走向一个更进步的联盟
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探索。我们在这里使用的父权制与其说是一个分析性的术语,更像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如果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做得不够,激进的女性主义本身也不够,那么我们就需要发展新的类别。我们的任务之所以是困难的,是因为同样的特征,如劳动分工,往往同时加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而在一个完全父权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很难分离出父权制的机制。然而,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指出一些起点:观察谁从妇女的劳动力中受益,揭示父权制的物质基础,调查男性之间的等级制度和团结机制。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能谈谈父权制度的运动规律吗?父权制是如何产生女性主义斗争的?除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在哪里还能看到性别政治和性别斗争?父权制度的矛盾是什么?它们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知道父权关系导致了女权运动,资本产生了阶级斗争一一但是女性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在历史背景下是如何发挥出来的呢?在本节中,我们试图提供对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 在历史上和现在,女性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要么就是两条完全独立的道路(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另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要么就是在左翼内部由马克思主义来支配女性主义。关于后者,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力量的结果,也是左翼内部男人的力量的结果。这些观点既产生了左翼的公开斗争,也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矛盾立场。 大多数认为自己是激进分子的女性主义者(反体制、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康米、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反)会同意,妇女运动的激进派己经失去了势头,而「资产阶级」似乎抓住了时机并继续前进。我们的运动已经不再处于那个令人兴奋的,精力充沛的时期,那时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有用:提高意识,把更多的女性(甚至比能容纳的更多)带入运动,在社会中增加女性问题的可见性,通常以一种在根本上挑战资本主义和父权关系的方式进行。现在我们感觉到女权运动的一部分被吸收了,「女性主义」被用来反对女性 一一 例如,在有些诉讼中法官主张女性离婚前是家庭主妇的也不需要赡养费,因为我们都知道女性现在已经被解放了。迄今为止未能通过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RA)表明,在许多女性心中仍存在一种立法上的恐惧,她们害怕「女性主义」将继续被用于针对女性,这表明我们真的需要重新评估我们的运动,分析为什么它以这种方式被吸收了。对我们来说,求助马克思主义来进行重新评估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它是一个发展着的社会变革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我们试图使用它时,我们有时也偏离了女性主义的目标。 左派一直对妇女运动持矛盾态度,经常认为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当左翼女性拥护女性主义时,它可能会对左翼男性构成个人威胁。当然,许多左翼组织也从妇女的劳动中受益。因此,许多左翼的分析(无论是进步的还是传统的)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自私的。它们试图影响妇女放弃对妇女的情况产生独立理解的努力,并采纳他们自己对情况的理解。至于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压力,当我们转向马克思主义分析,自然会试图加入使用这个范式的「兄弟会」,我们可能最终试图为与兄弟会的斗争正名,而不是试图用分析女性的情况来改善我们的政治实践。最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传统的女性问题的批判分析感到满意。他们认为阶级是理解女性地位的正确框架。妇女应该被理解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应该优先于男女之间的任何冲突。不能允许性(别)冲突干扰阶级团结。 随着过去几年美国经济形势的恶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也需要重新为自身正名。在60年代,民权运动、学生言论自由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运动、环保运动以及专业集团和白领团体日益激烈的运动都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新的问题。但现在,通货膨胀和失业等明显的经济问题的回归,掩盖了这些要求的重要性,并让左派回到了「基本盘」——(狭义定义的)工人阶级政治。很多到处生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党派小团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反女性主义者。有迹象表明,左翼学术界中女性主义问题的讨论程度也在下降。日间托儿所正在从左翼工会会议的讨论内容中消失。随着马克思主义或政治经济学在智力上被接受,自由主义学术界的老男孩网络被复制到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组成的年轻男孩网络中,尽管它年轻而激进,但在成员和观点上仍是男性式的。 那种让激进女性放弃这些愚蠢的东西,变得「严肃」的革命性的压力增加了。与「通货膨胀」和「失业者」相比,我们的工作似乎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女性)的失业从未被视为一场危机,这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症状。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次重大经济危机中,巨大的失业一部分是通过将女性排除在各种工作之外来解决的 —— 即每个家庭只有一个的工薪工作,而这份工作是男性的工作。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从危机中恢复了,也加强了。正如经济危机通过纠正失衡为资本主义发挥恢复作用一样,它们也可能为父权制服务。30年代让女性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如果放弃对女性主义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反对资本和父权制的斗争就不可能成功。一场仅仅针对资本主义压迫关系的斗争将会失败,因为它们在父权压迫关系中的潜在支持将会被忽视。对父权制的分析对于一种会破坏父权制的社会主义的定义是必要的,这种社会主义也是唯一一种对女性有用的社会主义。虽然男人和女人都需要推翻资本主义,但他们保留了性别群体特有的利益。从我们的研究、历史或男性社会主义者来看,尚不清楚「社会主义」所为之奋斗的东西对男人和女人是否都是一样的。因为一个「人道的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就新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和一个健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达成一致,而且更具体地说,它将要求男人们放弃他们的特权。 作为妇女,我们不能让自己被花言巧语哄骗住,从而放弃我们任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就像我们在历史中许多次被骗的那样。我们必须反对那种尝试让我们放弃女性主义之目标的明显的和不明显的高压。 这意味着两个策略性的考虑。第一,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是一场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组成联盟的斗争。妇女不应该相信男人在革命后「解放」他们,部分原因是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知道怎么做;一部分因为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做;事实上,他们的直接利益在于我们受到的持续压迫。相反,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权力基础。第二,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的性别分工给了女性一种实践,在其中我们已经学会了理解人类的相互依赖和需求是什么。我们同意莉丝·沃格尔的观点,即虽然男性长期以来一直在与资本作斗争,但女性知道该为 什么 而奋斗。[^59] 一般来说,男性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中的地位阻止了他们认识到人类对养育、分享和成长的需求,以及认识到在非等级制和非父权制的社会中满足这些需求的可能性。但即使我们提高了他们的意识,男人们也可能会评估潜在的收益和潜在的损失,然后选择现状。男人可能会失去的不只是单纯的枷锁。 作为女性主义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组织一种实践,既解决反对父权制的斗争,也解决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必须坚持,我们想要创建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相互依赖的认同是解放而不是耻辱,在其中养育后代不是一个压迫的实践而是一个普通的实践,在其中女性不再继续支持不正当的那些具体的男性自由。/ 注释:
[^1]: Often paraphrased as “the husband and wife are one and that one is the husband, “English law held that “by marriage, the husband and wife are one person in law: that is, the very being or legal existence of the woman is suspended during the marriage, or attest is incorporated and consolidated into that of the husband,"I.Blackstone,Commen-taries,1765,pp.442-445,cited in Kenneth attest attest attest Based Discrimination (Mann Publishing Co.,1974),p.117. [^2]: Friedrich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Engels, The Property and the Engels, The an introduction by Eleanor Burke Leacock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2). [^3]: Fri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58).See especially pp.162-166 and p.296. [^4]: Eli Lavretsky, “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Socialist Revolution, Arti in no.13--14 (January-April 1973),pp.66-125,and Part II in no.15 (May-June 1973).pp.19-70.Also Lavretsky, “Socialist Politics and the Family, “Socialist Revolution(now Socialist Review),no.19 (January-March 1974),pp.83-98,and 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New York: Harper Row,1976).Insofar as they claim their analyses are relevant to women, Bruce Brown's women, Bruce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3)and Henri Lefebvre's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Harper Row,1971)may be grouped with Lavretsky. [^5]: In this Lavretsky is following Margaret Benst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 “Monthly Review,vol.21,no.4 [September 1969],pp.13-27),who made the cornerstone of her analysis that women have a different relation to capitalism than men. She argued that women at home produce use values, and that men in the labor market produce exchange values. She labeled women's work precapitalist (and found in women’s common work the basis for their political unity).Lavretsky builds on this essential difference in men's and women's work, but labels them both capitalist. [^6]: Lavretsky, “Personal Life,”PartI,p.114. [^7]: Maria Rosa Dalla Costa,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by Maria 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Power of WA Press,1973;second edition)pamphlet,78 pp. [^8]: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in the original article (cited in n.7 above)Dalla Costa suggests that wages for housework would only further institutionalize women's housewife role (pp.32,34)but in a note (n.16,pp.52-53)she explains the demand's popularity and its use as a consciousness raising tool. Since then she has actively supported the demand. See Dalla Costa, “A General Strike, “in All Work and No Strike, “in Wages Dereddened Edmond and Suzie Fleming (Power of WallPress,1975). [^9]: The text of the article reads: “We have to make clear that, within the wage, domes-tic work produces not merely use values, but is essential to the production of surplus value"(p.31).Note 12 reads: “What we mean precisely is that housework as work is productive in the Marxian sense, that is, producing surplus value"(p.52,original emphasis).To our knowledge this claim has never been made more rigorously by the wages for rigorously Marxists have responded to the claim copiously. [^10]: The literature of the debate includes Lise Vogel, “The Earthly Family,"RadicalAmerica,Vol.7,no.4-5 (July-October 1973),pp.9-50;Ira Gerstein, “Domestic Workhand Capitalism, “Radical America,Vol.7,no.4-5 (July-October 1973),pp.101-128;John Harrison, “Political Economy of Housework, “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Economists,Vol.3,no.1 (1973);Wally Sercombe, “The Housewife and Her Lambourn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no.83 (January-February 1974),pp.3-24:MargaretCoulson,Branka Magas, and Hilary Wainwright, ‘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r neocapitalism’s Critique, “New Left Review,no.89 (January-February 1975),pp.59-71;Jean Gardiner, “Women’s Domestic Labor, “New Left Review,no.89 (January-February1975),pp.47-58;Ian Gough and John Harrison, “Unproductive Labor and Housework Again, “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Vol.4,no.1 (1975);Again, “Bulletin Homeliest and Maureen Mackintosh, “Women’s Domestic Labor, “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Vol.4,no.2 (1975);Wally Sercombe, “Domestic Sercombe, “Domestic to Critics, “New Left Review,no.94 (November-December1975),pp.85-96;Terry Fee, “Domestic Labor: An Analysis of Housework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roduction Proces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t.8,no.1(Spring 1976),pp.1-8;Susan Homeliest and Simon Mohan, “Domestic Labor and Capital,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no.I (March 1977),pp.15-31. [^11]: In the Upstate most often-heard political criticism of the wages for housework group has been its opportunism. [^12]: Laura Oren documents this for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Welfare of Women in Laboring Families:England,1860-1950,"Feminist Studies,Vol.1,no.3-4 (Winter-Spring1973),pp.107-25. [^13]: The late Stephen Hymers pointed out to us a basic weakness in Engels ‘analysis unoriginal weakness that occurs because Engels fails to analyze the favor process within the family. Engels argues that men enforced monogamy because they wanted to leave their property to their own chlorenchyma argued that far from being a "gift, “among the petit bourgeoisie, possible inheritance is used as a club to get children to work for bourgeoisie, possible must look at the labor process and who benefits from the labor of which others. [^14]: This is a paraphrase. Karl Marx wrote: “The maintenance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s, and must ever be, a necessary condition to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 But the capitalist may safely leave its fulfillment to the laborer’s instincts of self-preservation and propagation."(Capit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7],Vol.1,p.572.) [^15]: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5). [^16]: Juliet Mitchell, Women’s Estate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73),p.92. [^17]: York: Vintage to the First Edition,"pp.71-72.The continuation of this quotation reads’”. By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labor on the one hand and of the family on the other. “It is interesting that, by implication, labor is excluded from occurring within the family; this is precisely the blind spot we want to overcome in this essay. [^18]: Juliet Mitchell, “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no.40(November-December 1966),pp.11-37,also reprinted by the New England Free Press. [^19]: Juliet Juliet and Femin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74). [^21]: Shulamite Firestone, The Dialectic aft Sex (New York: Bantam Books,1971). [^22]: Polities of Ego: A Manifesto for New York Radical Feminists be founder founder Honed Ellen Levin (New York: Quadrangle Books191,pp.440-443."Radical feminists’ those feminists who argue that feminists’ dynamic of history is men's string Toom women. “Toom women anti-women. “Toom but has the specified this picross picross decal feminisms whom the New York Radical Feminists were probably York Radical be found in Radical York Radical Kode(New York:QuadranglePress,1972). [^23]: Focusing on power was an important step forward in the feminist critique Kode argues, for example, that if little example, that it was because they recognized that lite boys grew uptore members of a powerful class and little grew up to be dominated by little grew crossways the heart of crossways ecofeminists have criticized Firestone for rejecting the ecofeminists concept of the unconscious. In seeking to explain the strength and continuation of male dominance, recent feminist writing has prophesized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gender-based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their origins in the unconscious, and the consequent difficulty of their eradication. See Dorothy Dinnerstein, 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1977),Nancy Chodorow,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and Jane Flax, “The Conflict Between Nurturance and Autonomy in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s and Within Knish Studies,Vol.4,no.2 (June 1978),pp.141-189. [^24]: 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New York: Avon Books,1971),p.25. [^25]: One example of this type of radical feminist history is Susan York: Avon Our York: Avon Rape (New York: Simon Schuster,1975). [^26]: For the bourgeois social science view of patriarchy, see ,for example ,Weber’s distin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legal authority, Max Weber: The Theori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64),pp.328-357.These views are also discussed in Elizabeth Fee, “The Sexual Politics of Victorian Social Anthropology, “Feminist Sudies,Vol.1,nos.3-4(Winter-Spring 1973),pp.23-29,and in Robert Anisett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1966),especially Chapter 3,"Community." [^27]: See Viana Muller,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a Case Study in England and Wal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9,no.3(Fall 1977),pp.7-21. [^28]: The particular ways in which men control women's access to important of Radical and restrict their sexuality vary enormously, both from society to society-group to sub-group, and across time. The examples we use to illustrate patriarchy in this section, however, are drawn primarily from the experience of whites in we stem capital-its countries. The diversity is shown in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untries. The Rei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5),Woman, Culture and Woman, Culture Rosado and Louise Lamp here (Lamp here University Press,1974),and Lamp here: A Biosocial Approach, by Lila Leibowitz (Approach, by Press,1978). The control of women's sexuality is tightly linked to the place of childre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emand (by men and capitalists)for children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changes in women's subordination. Where children are needed for their present or future labor power, women’s sexuality will tend to be directed towards reproduction and child-rearing. When children are seen rearing. When sexuality for other than reproductive purposes is encouraged, but men will attempt to direct it toward satisfying male needs. The Cosmo girl is a good example of a woman "good example child-rearing only to find herself turning at her energies towards attracting and satisfying men. Capitalists can also use female sexuality toothier own ends, as the success of Cosmo in advertising consumer products shows. [^29]: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in Anthropology of Women,ed.Reiter,p.159. [^30]: Homeliest and Mohan point out that both aspects of production (people and things)are logically necessary to describe a mode of production because by definition amide of production must be capable of reproducing amide aspect alone is amide put it simply the production of things requires people, and the production of people requires production recognizing capitalism's need for production concern himself with how they were produced or what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aspects of production were. See Homeliest and Mohan, “Domestic Labor and Capital"(note 10 above). [^31]: For an excellent discussion of one such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see socialism, see, “Women in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as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8,no.1 (Spring 1976),pp.34-58. [^32]: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in the pre-industrial period, women contributed a large share to their contributed-either by participating in a family craft or by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The initiation of wage work for women both al-lowed and required this contribution to take place independently from the men in activities. The new activities. The not that women earned income, but that they did so beyond their husbands ‘or husbands’ or Clark, The Working Life of Wome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Kelly,1969)and Ivy Pinchbeck, Women Worker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50-1850 (New York:Keily,1969)describe women's pre-industrial economic roles and the changes that occurred as capitalism progressed. It seems to be the case that progressed. It progressed. It fully aware of women's economic role before capitalism. [^33]: Karl Koutekite Class Struggle (New York:Norton,1971),pp.25-26. [^34]: We might add, “outside the household, “add, “outside Struggle,p.26,our emphasis. [^35]: Cited in Neil Smelser, Social Chang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p.301. [^36]: These examples are from Heidi Chicago: University: University Job Segregation by Exscind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Vol.1,no.3,pt.2(Spring1976),pp.162-163. [^37]: Just as the factory laws were enacted for the benefit of all capitalists against the protest of some, so too, protective legislation for women and children may have been enacted by the state with a view toward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Only a completely instrumentalist view of the state would deny that the factory laws and protective legislation legitimate the state by providing concessions and are responses to the demands of the working class itself. [^38]: For a more complete discussion of protective labor legislation and the demands the demands Labor Legislation for Women: Its Origin and Effect, “Mimeographed (New Effect, “Mimeographed Law School,1970)parts of which have been published in Barbara been published been published Houstonian Susan Cross-sex Discrimination and the Law: Cases and Remedies (Boston:Little,BrownCo.,1975),an excellent law text. Also see Hartmann, “Job Segregation by Sex,"pp.164-166. [^39]: A reading of Laic Clark, The Working Life of Women, and Ivy Pinchbeck, Women Workers, suggests that the expropriation of production from the home was fool-lowed by a social adjustment process creating the social norm of the family fool Capitali.sm and Women's Work in the Home,1900-1930(Unpublished fool University,1974;forthcoming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0)resailed on qualitative data, that this process occurred in the U.S.in the early 20thentury.One should be able to test this hypothesis quantitatively by examining familied studies for different years and noting the trend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family come for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provided by the groups, provided data Istio available in comparable form for our period. The "family wage “resolution has probably been undermined in the post World War If period. Carolyn Shaw period. Carolyn Women's Contributions to Family Income,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ol.1,no.3 (July 1974),pp.185-201,presents current data and argues that it is noncorrect to assume that the man is the primary earner in the family. Yet whatever textual situation today or earlier in the century, we would argue that the social norm was and is that men should earn enough 1o support their families. To say it has been the norm is not to say that it has been universally achieved. In fact, it is precisely the failure to achieve the norm that is noteworthy. Hence the observation that in the absence of sufficiently high wages, “normative “family patterns disappear, as disappear, as immigrant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ird world disappear, as Handlin, Boston’s Immigrants (New York:Atheneum,1968)discusses-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where Irish women were employed in textiles; women constituted more than half of ail wage laborers and often supported unemployed husbands. The debate about family structure among Black Americans todays Ili rages; see Carol Stickb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immunity (New York: Harper Row,1974).esp.Chap.1.We would also argue (see that for most families the norm is upheld by the relative places Menand below)men hold in the labor market. [^40]: Hartmann, “Job Work, argues that the non-working wile was generally re-graded as part of the male standard of liv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ee p.136,n.6)and Gerstein, “Domestic Work, “suggests that the norm of the working wife enters in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value of male labor power (see p.121). [^41]: The importance of the fact that women perform labor services for men in the home cannot be overemphasized. As Pat Maynard said in "The Politics of Housework,""[t]he measure of your oppression is his resistance"(in Sisterhood is he measure Morg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70],p.451).Her article, perhaps as important for us as Firestone on love, is an analysis of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women and men as exempli-feed by housework. [^42]: Libby Zimmerman has explored the relation of membership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labor markets to family patterns in New England. See her Women in theonomy’s Case Study of Lynn,Massachusetts,1760-1974 (Unpublished theonomy’s School,Brandeis,1977).Batia Weinbaum is currentl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roles and places in the labor market’s her "Rede-fining the Question of Revolu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9,no.3 (Fall 1977),pp.54,78,and The Curious Courtship of Women's Liberation and Social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1978).Additional studies of the interaction of capitalism and patriarchy can be found in Zillah of capitalism capitalism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8). [^43]: See Batia Weinbaum and Amy Bridges, “The Other Side of the Bridges, “The Capital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sumption, “Monthly Review,Vol.28,no.3 (July-August 1976),pp.88-103,for a discussion of women's consumption work. [^44]: For the view of the Frankfurt Chooses Max Horkheimer, “Authority and the Family, “in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Herder Herder,1971)and Frankfurt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The Family, “in Aspects of Sociology (Boston:Beacon,1972). [^45]: Carol Brown, “Patriarchal Capitalism and the Female-Headed Family, “Social Scientist (India),no.40-41 (November-December 1975),pp.28-39. [^46]: For more on racial orders, see Stanley Greenberg. “Business Enterprise in a Racial Order, “Politics and Sociery,Vol.6,no.2 (1976),pp.213-240,and Michael Burroway, The Color of Class in the Copper Mines: From African Advancement to Labialization(Labialization University Press, Zambia Papers No.7.1972). [^47]: See Michael Reich, David Gordon, and Richard Edwards, “A Theory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3.no.2 (May 1973),pp.359-365,and the book they edited, Labor Marker Segmentation (Lexington,Mass.:D.C.Heath,1975)for a discussion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48]: See David segmentation Efficiency and Socialist Efficiency,"MonthlyReview,Vol.28,no.3 (July-August 1976),pp.19-39,for a discussion of qualitative efficiency (social control needs)and quantitative efficiency (accumulation needs). [^49]: For example, Milwaukee manufacturers organized workers in production first according to ethnic groups, but later taught all workers to speak English, as technology and appropriate social control needs changed. See Gerd changed. See changed. See View from Milwaukee,1866-1921(Madison: The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1967). [^50]: Carol Brown, “Patriarchal Capitalism." [^51](New York : Random House, 1976 .) [^52]: Jean Gardiner, in "Women's Domestic Labor"(see n.10),clarifies the causes for the shift in location of women's labor, from capital's point of view. She examines what capital needs (in terms of the level of real wages, the supply of labor, and the size of markets)at various stages of growth and of the business cycle. She argues that in times of boom or rapid growth it is likely that socializing housework (or more accurately capitalizing it)would be the dominant tendency, and that in times tendency, and will be maintained in its traditional form. In attempting to assess the likely direction of the British to assess does not assess the economic needs of patriarchy. We argue in this essay that unless one takes patriarchy as well as capital into account one cannot adequately assess the likely direc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53]: For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in nuclear families, see Peter Muhlenberg, “Cohort Variations in Family Life Cycle Experiences of Muhlenberg, “Cohort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Vol.36,no.5 (May 1974),pp.284-292.For remarriage rates see Paul Click and Arthur Click on the Recent Upturn in Divorce and Remarriage,"Demography,Vol.10 (1974),pp.301-314.For divorce and in-come levels see Arthur Norton and Paul Norton Norton Futur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Vol.32,no.1 (1976).pp.5--20.Also see Mary Jo Bane, Here to Stay: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1976). [^54]: Heather Loess and Isabel Loess of Transition: The Growth of Fame-lies Headed by Women (Fame Urban Institute,1975). [^55]: See Kathryn Walker and Margaret Woodstone Use: A Measure of House. Hold Production of Family Goods and Services (House. Hold Home Economics Association,1976). [^56]: Richard Sennett's and Johnathan Cobb's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Home Economics House,1973)examines similar kinds of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within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n at work. [^57]: This should provide some clues to class differences in sexism, which we cannot explore here. [^58]: See John Steeleye at., Crestwood Height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Press,1956),pp.382-394.While men's place may be characterized as "in production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omen's place is simply ‘not in production"-her simply ‘not by capital. Her non-wage work is the resolution, on a day-to-day basis, of production for exchange with socially determined need, the provision of use values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this is the context of consumption).See Weinbaum and Bridges,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ycheck, “for a more complete discussion of this argument. The fact that women provide "merely “use values in a society dominated by exchange values can be used to denigrate women. [^59]: Lise Vogel, “The Earthly Family"(see n.10).  点亮「在看」,让更多人看到
点亮「在看」,让更多人看到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Philosophia 哲学社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scieok.cn/post/3625.html
-
- 「实行一切与现实截然相反的」:欧洲哲学中的野蛮人形象(上)
- 实质的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分别是什么? /翻译
- 对环境保护阴谋论的逻辑分析|随笔
- “女权文书”成Top 20“金钥匙”?你连伪女权都辨认不出,别做梦了!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快婚姻 —— 走向更进步的联合体 / 翻译
22288 人参与 2022年11月06日 12:44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



